
摘 要: 20世纪初,英帝国联邦建设的困境与英帝国团结的诉求推动了帝国教育事业的前行。这项事业旨在达成的目标不是建立统一的联邦,而是构造合作的联盟,所以注重英帝国成员间无形情感纽带的营造。“皇家殖民协
摘 要: 20世纪初,英帝国联邦建设的困境与英帝国团结的诉求推动了帝国教育事业的前行。这项事业旨在达成的目标不是建立统一的联邦,而是构造合作的联盟,所以注重英帝国成员间无形情感纽带的营造。“皇家殖民协会”在以教育来维系英帝国团结的思路及“帝国协会”工作的启发下,投入帝国教育活动当中。它除了关心面向大众的帝国教育外,还注重在大学中开展帝国教育与研究,因此促成了一场“帝国研究运动”。该运动的核心内容是英帝国史的研究与教育。出于捍卫帝国的目的,学者们借助历史书写,强调了不列颠人的种族特殊性和优越性,并为英帝国的统治辩护。此后,这些因素进入英国社会舆论当中,影响深远。
《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秋季号
19世纪后期,英帝国面临着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境内多地出现了公开叛乱,境外利益则受到了新崛起国家的威胁。面对挑战,英国社会里出现了焦虑情绪,担忧“我们昨日的盛景,与尼尼微和推罗一道湮灭”。政治家愈发强调英帝国与每一个英国人的利益息息相关,若帝国瓦解,“我们大部分人口还能生活下去吗?”在此情形下,各种捍卫英帝国的方案开始出现。围绕着英帝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有人支持构建有形制度,营造统一国家;有人认可鼓舞帝国情感,发展相互合作的关系。到20世纪初,后者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并成为1926年“大英国协”(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架构的灵感来源。那么这一转变如何实现,特别是哪些重要因素参与到20世纪初英帝国无形情感纽带的塑造过程之中呢?
学界对上述阶段中英帝国团结方案的研究丰富且深入,主要关心“帝国联邦”(Imperial Federation)与其他致力于帝国统一的设想,以及建设“更大的不列颠”(Greater Britain)的多种努力。不过,仍存在可以推进的学术空间。其中,由于帝国教育在培育情感纽带、维系英帝国团结过程里发挥了关键作用,所以有哪些组织、个人参与其中,各自具有何种特点,成为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詹姆斯 · 格林利(J. G. C. Greenlee,1945—)的几项研究中,帝国教育的概况得到了勾勒。从中可见,20世纪初多个关注英帝国命运的协会投身到这项事业当中,“皇家殖民协会”(Royal Colonial Institute)也不例外。在讨论该协会的作用时,“帝国研究运动”(Imperial Studies Movement)也得到了介绍。
“帝国研究运动”兴起于1914年,延续至20世纪20年代末,它对于专业英帝国史研究的形成至关重要。在其直接影响下,伦敦国王学院设立了罗德斯帝国史教授席位(Rhodes Professorship of Imperial History)。随后,专业英帝国史研究也在大学里逐渐站稳脚跟。然而,怎样的历史语境塑造了该运动,以及作为该运动核心成果的英帝国史书写具有哪些特质等关键问题仍然未得到仔细考察。本文将把上述问题作为主要思考对象,第一部分主要考察20世纪初帝国教育事业的兴起,勾勒促使“皇家殖民协会”转向教育工作的历史语境。第二部分围绕“皇家殖民协会”转向教育事业后实施的多个项目展开论述,探究“帝国研究运动”兴起的具体原因及主要内容。由于英帝国史在此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第三部分将讨论在“帝国研究运动”影响下得到发展的英帝国史书写的特质。通过对这三个部分的分析,本文试图从一个侧面展现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者借助教育手段捍卫帝国,进而以历史叙事来赋予自身行为合理性的种种努力。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偏重以“自上而下”的角度,分析主事者的观念与策略,至于受众方的接受、理解或运用知识的情况并不在论述的范围内。
01
转向教育:捍卫英帝国的新思考
1915年,时任“帝国协会”(League of Empire)主席的弗里德里克 · 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1845—1937)在回顾过去一段时间内的成绩时着重提出,布尔战争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团结英帝国的方案,帝国教育事业由此起步,“帝国协会”也应运而生。与“转向教育”的趋势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于未来英帝国的政治秩序有了新的看法。换言之,关于英帝国政治秩序的新看法也激发了帝国教育事业。
首先,有关英帝国政治秩序新看法的出现,与帝国统一化实践的衰微直接相关。19世纪后期,英国本土与自治殖民地(self-governing colony)内掀起了“帝国联邦运动”(Imperial Federation Movement)。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囊括大不列颠、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在内的联邦制国家。约翰 · 西利(John Robert Seeley,1834—1895)在1883年出版的《英格兰的扩张》为以上运动提供了历史依据与理论支撑。在西利看来,从英格兰发展为英帝国的过程既是地域的扩展,也是民族的扩散,所以在“共同的血缘、信仰与利益”基础上,英帝国应当且能够成为一个联邦制的“世界国家”(world state)。“帝国联邦运动”的支持者在西利的启发下热衷于构想帝国的有形制度,希望英帝国发展成统一民族国家。但在运动内部路线不一,组织方财政紧张,殖民地意愿不强与政策落实难度太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帝国联邦运动”在19世纪末逐渐式微。1893年12月31日,伦敦的“帝国联邦协会”(Imperial Federation League)最终解体。
在“帝国联邦运动”的实践遭遇困境的同时,其民族国家式的政治构想也受到了质疑。早在1885年,爱德华 · 弗里曼(Edward A. Freeman,1823—1892)就指出“帝国联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进入20世纪,热衷帝国团结事业的人士纷纷认为营造联邦制帝国,特别是创建帝国议会(Imperial Parliament)的构想日渐脱离现实。例如曾长期关注帝国宪政问题的弗里德里克 · 波洛克就一改既往态度,转而关注帝国成员间的情感纽带。他认为目前各殖民地内本土意识日益高涨,这使得任何以统一国家为目标的帝国团结计划均难以实现。
其次,有关英帝国政治秩序新看法的出现,也与英帝国主义者的思想回应有关。在所有相关思考中,理查德 · 吉布(Richard Jebb,1874—1953)的观点最引人注意。吉布在1905年出版了《殖民地民族主义研究》。凭借该书,他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帝国问题专家。与西利秉持的民族国家式政治构想不同,吉布认为各殖民地内兴起的本土民族意识已不容忽视,未来英帝国的团结必然要建立在多元民族主义之上,这势必导致帝国联邦计划的破产,因此自治殖民地与大不列颠合构为“联盟”(alliance)是更加现实的出路。而联盟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英帝国成员间共享了物质利益、生活方式与精神遗产。在他看来,殖民地内蕴含的“帝国的灵魂”使民族与帝国、殖民地与母国间具有内在统一性。在共享的精神遗产下,吉布认为未来的英帝国理应是由平等成员团结而成的“联盟”。由于他将捍卫帝国的希望寄托于“无形纽带”,所以格外注重帝国教育事业。在吉布看来,通过教育来消除英帝国境内各地民众间的误解,并纠正不列颠岛内舆论对自治殖民地的偏见或无知是迈向帝国团结的第一步。
在上述两者的作用下,帝国教育事业在20世纪初走向台前。回顾过往,“帝国教育”一词鲜少在公共媒体上露面。虽然“帝国教育大会”(Imperial Education Congress)曾于1897年在伦敦召开,但是会上讨论的问题局限于妇女的卫生、农业训练。进入20世纪后,帝国教育才成为时兴议题,媒体报道中教育对捍卫帝国的价值得到突出,众多帝国主义者也将视线转至教育话题。埃德蒙 · 萨金特(Edmund B. Sargant,1855—1938)认为“更大的不列颠”想要变为现实,就必须从帝国教育开始做起,具体的方针包含设立教师交换制度、专门的奖学金以及帝国教育联盟。理查德 · 霍尔丹(Richard Haldane,1856—1928)也投身帝国教育事业。他同样认为应当以帝国教育联盟的名义组织教育大会,发展殖民地教育,并创设旨在鼓励学生周游帝国的奖学金。除个人外,多个新兴协会也把帝国教育事业当作新的工作重心。
为增进帝国成员间的相互了解,“帝国协会”率先策划了多个项目。其中,最为关键的是1907年召开的“联邦教育大会”(Feder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会议以帝国教育与帝国团结的关联为主旨。克鲁勋爵(Lord Crewe,1858—1945)在开幕式上就强调为了提升民众的帝国热情,帝国教育事业刻不容缓。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的院长更是把此次集中讨论帝国教育的会议视为走向帝国团结的第一步。他认为在帝国教育事业的开展下,一幅和谐的图景一定会出现,到那时:
来自新西兰、澳大利亚或南非的孩子能熟悉英格兰的城市、纪念碑和风景,了解背后古老的荣耀与合作精神。同样,来自英格兰乡镇、苏格兰港湾、爱尔兰或威尔士山区中的孩子也能了解加拿大麦田与高地、南非或澳大利亚平原上同胞们的生活。另外,米思勋爵(Lord Meath,1841—1929)认为此次半官方性质的会议比此前召开的帝国会议(Imperial Conference)更重要,因为帝国教育的意义更深远,能够塑造孩童的心灵、意识和感情,使伟大的英帝国成为人们脑海中的理想。除了不列颠本土人士外,殖民地代表也积极参与,并将此次活动看作交流经验、团结帝国的重要机会。
帝国教育事业的热心人士认为英帝国史是这项事业的核心,因此“联邦教育大会”设有以约翰 · 伯里(John B. Bury,1861—1927)为主席的历史分会。在分会场上,伯里首先认为如今的历史教育有了更重大的使命,如树立公民责任感、培养英帝国成员间的情感纽带等,因此加强英帝国史教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其首要步骤是改革现有历史教育模式,摆脱记诵的重负,强调情感道德熏陶的价值。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的代表也指出历史教育长期以来固守僵化的教学模式,这不符合现今捍卫帝国的需求。其次,赫伯特 · 费舍尔(Herbert A. L. Fisher,1865—1940)重申了西利所谓“历史是政治才能的学校”的名言,认为历史教育要突出“英国人与帝国文明的伟大之处,它的成长发展以及随后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而这不仅要在本土大学里讲授,还要进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课堂当中,以加强大学生之间的情感与知识纽带。另外,哈尔福德 · 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 1861—1947)则强调地理学、世界历史、帝国政治史教育的结合既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认识帝国各地的情况,又有利于形塑整体性的英帝国观念。此外,编写英帝国史教材的计划也被提上议程,会议代表指出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要编纂不同类型的教材,它们既要涵盖过往,还要涉及当下,“帝国协会”是主持教材编写的合适组织。
John Robert Seeley, 1834-1895
伴随着编写教材的呼声,“帝国协会”资助了一批相关著作的出版,以满足帝国教育的需求。教材《英帝国:过去、现在与未来》于1909年出版。在序言里,主编阿尔伯特 · 波拉德(Albert Pollard,1869—1948)说道:
本书目的在于知识的提升,当然更重要的目的是在不刻意歪曲事实及漠视帝国问题的前提下,提供尽可能精简的信息,进而加强对帝国本身及其何以形成的理解。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是为进一步的帝国史教育作预备。
两年后,《英帝国和它的历史》与《帝国的故事》在“帝国协会”的帮助下出版。这两部适用于中小学的教材旨在培养未来的英帝国公民,因而尽可能减轻记诵的负担,转而突显帝国的责任和帝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除此以外,弗里德里克 · 柯克帕特里克(Frederick A. Kirkpatrick,1861—1953)撰写的《英国殖民化和帝国讲演录》和威廉 · 司佳德(William K. Stride, 1865—1936)创作的《帝国建设者》也在“帝国协会”的资助下出版。它们均是简明的大众读物,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前者还配有幻灯片。
帝国教育事业的推动者对捍卫英帝国充满信心。他们认为,尽管英帝国难以成为统一国家,但帝国瓦解却非必然命运,在帝国教育,尤其是英帝国史教育下,帝国成员间的无形纽带将更为坚韧。波洛克在总结“帝国协会”的阶段性工作时指出,每四年召开一次的“联邦教育大会”,英帝国史教材和论著的出版,“帝国教师协会会议”(Imperial Conference of Teachers’ Associations)和“帝国教师联盟”(Imperial Union of Teachers)的成立为此做出了主要贡献。在此氛围下,“皇家殖民协会”投入到帝国教育事业当中,“帝国研究运动”也得以兴起。旨在突显精神纽带,强调帝国公民责任的英帝国史书写自然也贯穿其中。
02
“皇家殖民协会”与“帝国研究运动”的兴起
在19世纪70和80年代,“皇家殖民协会”曾是“帝国联邦运动”的中心。在关于英帝国问题,如英帝国政治结构、贸易、劳工移民的讨论中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在该阶段里,协会多位重要成员参与创立了“帝国联邦协会”,并组织了多场以帝国联邦为主题的会议。但随着“帝国联邦运动”逐渐衰落,“皇家殖民协会”对联邦制的态度也转向质疑,个别成员只能在组织外,以个人身份继续探索统一化方案。在协会淡出“帝国联邦运动”后,帝国教育事业成了新的工作重心。
首先,“皇家殖民协会”工作重心的转移与时代氛围密切相关。20世纪初,也就是“联邦教育大会”闭幕后,“皇家殖民协会”开始大力推进帝国教育事业。原先为“帝国联邦运动”摇旗呐喊的乔治 · 帕金(George Robert Parkin,1846—1922)此时就提到,若英帝国不把情感联系作为基础,那么任何形式的纽带都将失效,因此当务之急是培养民众的帝国情感。
出于建设帝国情感纽带的目的,协会将“帝国协会”视为榜样,试图发挥其帝国知识交流中心的功能,因而大力扩充自己图书馆的馆藏。为方便成员交流,协会在1910和1912年分别创办了《团结帝国》(United Empire)与《年鉴》(Year Book)。自1913年起,协会设立了研究与论文奖金,以鼓励更多人投入帝国教育和研究事业。评委则由牛津大学首任拜特殖民史教授(Beit Professor of Colonial History) 休 · 艾 格 顿(Hugh Edward Egerton, 1855—1927)担任。从历年指定选题与获奖作品的情况上看,迫切的时代议题引人关注,例如英帝国的优越性,即它为何能兼容自由与团结是被讨论最多的话题。如1913年,参选“科学探索金奖”(Gold Medal for Scientificc Inquiry)的文章就围绕以下问题展开:
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与其对外关系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以此作为出发点,不管英帝国是否具有更加中央化的政府体系,其自治领地在缺乏以贸易合作为目标的前提下,能不能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维持永久性的防卫合作关系。
又比如1914年,参选“科学探索金奖”的文章要对“民主制难以管理一个帝国”的问题做出回应。
其次,“皇家殖民协会”工作重心的转移还与该组织的人事变动有关。由于协会理事会的成员资格是终身制,因此在创立后,协会领导层变动很小,行事作风日趋保守,引起了其他会员的不满。在19世纪最后几年,如首任主席伯里子爵(Viscount Bury, 1832—1894)等一批创会元老相继辞世。这恰好为改革提供了有利条件。随后,协会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组建更高效的理事会;吸收女性成员;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分会;与商业组织发展更紧密的关系;推广帝国教育、宣传帝国理念,以吸引年轻人的兴趣。上述改革使协会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比如理事会主席的选举更为民主,会员人数上升,收入增长,与社会大众及其他协会的关系变得更紧密。最为重要的是,这使得协会更能回应时代的变化,并将开展帝国教育及传播帝国理念当作工作重心。
时代氛围和人事变动促使“皇家殖民协会”开展帝国教育。它的首个重要项目是在1910年创设的旨在普及帝国知识的“帝国讲座”(Empire Lecture)。“帝国讲座委员会”负责项目的决策,赫伯特 · 加里森(W. Herbert Garrison)负责具体实施。
在加里森的具体安排下,“帝国讲座”成绩斐然。从项目创设当年加里森所拟定的主题上看,讲座内容涵盖英帝国全境,内容以知识普及为主,开办的地点也遍及不列颠岛。借此机会,他也与其他机构频繁交流,并试图吸引更多人投身其中。随后,“帝国讲座”项目继续发展。1911年,讲座增加了新主题,其内容除了介绍英帝国的概况外,还着意凸显了帝国的意义与价值,以及帝国公民的责任。考虑到许多听众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也从未踏出过本土,加里森特意使用了自己收集到的100多张幻灯片,使讲座更为生动。同时,讲座还得到了上层人士的认可,多场讲座的主持人即为政界精英。在项目如火如荼开展的情况下,协会收入大增。乘此机会,策划者不但希望在更多中心城市里开设讲座,还试图招揽年轻人充当新讲师。1912年,除了在小市镇、夜校里开办讲座外,加里森还与地方学术组织开展合作,共同推广帝国教育。随着讲座的进行,加里森的努力得到了学界人士的注意,剑桥大学的弗里德里克 · 马什(Frederick H. Marsh,1839—1915)就认为加里森为大家讲述了“有史以来最奇妙的故事”。在可观成绩下,项目成员及资金得以扩充。随后几年,加里森的讲座依旧人满为患,他还颇有新意地将电影引入教学中。在火热的“帝国讲座”影响下,“皇家殖民协会”不断壮大。
“帝国研究运动”的兴起与成绩斐然的“帝国讲座”直接相关。可以说“帝国讲座”的成功使帝国教育事业有了坚实的基础,也使“皇家殖民协会”对类似工作更有信心,因而开始探索新的帝国教育计划。加里森的讲座面向普通大众,听众也多属年轻人,因此不涉及重要理论话题,只是普及帝国知识与强调帝国情感,风格具有“草根性”。对此,为更深入地推进帝国教育,协会试图借助专业学者的力量,将相关知识引入大学教育体系当中,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帝国教育。由此,“帝国研究运动”的计划被提上议程。
那么“帝国研究运动”将在哪个大学里萌生呢?19世纪末,英国的古老大学(ancient university)中已出现了程度不一的帝国教育成分。最知名的是,1881年秋与1882年春,西利在剑桥大学里开设了名为“英格兰的扩张”的课程。但因种种原因,殖民帝国史的教授席位并未借此机会在剑桥大学中设立起来,西利也没有就此掀起一场英帝国史教育的热潮。与之不同,牛津大学素与英帝国建设事业相关联,并率先设立了殖民帝国史教授席位。首任拜特殖民史教授休 · 艾格顿在一次由“皇家殖民协会”组织的会议上大谈牛津大学与英帝国的关系。他认为大学在强化帝国精神纽带的工作中要扮演关键角色,比如以奖学金的方式建构人才网,发展英帝国史教育,从而培养出怀揣“泛不列颠理念”(Pan-Britannic idea)的精英人士。他的演讲引起了众多“皇家殖民协会”成员的共鸣。但“帝国研究运动”并没有把牛津大学作为活动中心,而是将根据地安在了伦敦。这与西德尼 · 若(Sidney Low, 1857—1932)的建议直接相关。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Forgotten Books,2017)
西德尼 · 若在“皇家殖民协会”将帝国教育引进大学的过程里发挥了关键作用。他素来关心帝国问题,认为殖民地民族主义的成长无碍于英帝国的团结。针对帝国研究与教育的边缘地位,他呼吁英国所有大学都应把英帝国史升级为必修课,并设立更多以英帝国为讨论对象的教席,以推进帝国研究,使英帝国的政策能建立在坚实的学理基础上。关于这项事业的根据地,西德尼 · 若指出伦敦是英帝国的中心,学术资源丰富,能为帝国研究的开展提供帮助,因此该地应当成为“帝国研究运动”的根据地。另外,他认为运动组织方也不必以独立形式出现,只需借用现有条件即可。
西德尼 · 若的观点启发了“帝国研究运动”。在“皇家殖民协会”帮助下,1914年,阿尔弗雷德 · 米尔纳(Alfred Milner,1854—1925)、乔治 · 帕金及亨利 · 迈耶斯(Henry Miers,1858—1942)等人在伦敦大学创立了“帝国研究委员会”(Imperial Studies Committee)。在委员会运作下,名为“帝国研究讲座”(Imperial Studies Lectures)的教学项目建立,“讲座小组委员会”(Lectures Sub-Committee)也随之组建。“帝国研究运动”正式兴起。
与“帝国讲座”不同,“帝国研究讲座”旨在大学中讲授英帝国的历史与现实,影响精英阶层,进而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推进帝国教育,所以主讲者都是学院中的专家,而非加里森一般的非专业人士。讲座的地点也都在学院之中。如查尔斯 · 卢卡斯、赫伯特 · 费舍尔和阿瑟 · 史密斯(Arthur Smith,1850—1924)在伦敦大学里分别讲授“帝国与民主”“依附殖民地的管理”和“民众与帝国的责任”。
随后几年里,“帝国研究讲座”取得了显著成绩。卢卡斯曾在阶段性总结里首先指出以往大学教育中对英帝国欠缺关注,学生对其茫然无知的现象已在“帝国研究运动”的开展下大为改观。其次,他设想了运动的发展方向,希望将其推广到英国其他地方。在之后几年里,以上设想最终实现,例如伯明翰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及谢菲尔德大学中都出现了“帝国研究讲座”。即使是世界大战也没能阻碍讲座的进行。在主持者看来,战争反而对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具体而言,战争爆发后,英帝国问题更能吸引听众的注意,越来越多的大学内开设了“帝国研究讲座”,讲座数量不降反升,主题紧扣时事,如“帝国的整合”“帝国的通信与战争”“英国民主与帝国政策的控制”“加拿大与帝国的战争”。此后,在主讲者人数增多的情况下,更多大学被纳入计划。“皇家殖民协会”的图书馆也开放给有志于帝国研究的伦敦大学学生使用。面对丰硕成绩,阿瑟 · 牛顿认为讲座内容兼具科学与想象力,在其作用下,帝国教育,特别是英帝国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他看来,随着相互认知的提升,英帝国成员间的情感纽带无疑会日益坚韧,英帝国也将迎来光明的未来。
随着“帝国研究运动”的进行,其成果不再限于英国本土,海外的大学也开始关心帝国教育。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历史学“初级公共考试”(Junior Public Examination)中有百分之四十的问题涉及帝国史,以获得荣誉学位为目标的学生也需选修“英国殖民史对政治理论的影响”专题。另外,在日常教学中,与英帝国相关的内容也开始占据较大比重,例如大学三年级课程里就包含了“殖民地宪政的兴起与特点”的讲座,政治科学课程中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涉及帝国问题,经济学课程里也格外突出帝国经济的议题。
改革后的“皇家殖民协会”更为开放,更乐于和其他协会合作。“帝国研究讲座”因此得到了诸如“帝国协会”、“维多利亚协会”(Victoria League)的支持,更多关心英帝国的精英人士加入项目之中。“帝国研究委员会”的成员随之扩充,并进一步细分为三个“小组委员会”,即“大学、研究与成人资讯小组”(Universities, Research, Adult Information)、“公学与预备学校小组”(Public and Preparatory Schools)、“中学、继续教育学校与师范学院小组”(Elementary Schools, Continuation Schools, and Training Colleges for Teaching)。
随着“帝国研究讲座”的广泛开展,“皇家殖民协会”在整个帝国教育事业里的角色愈加重要。它甚至想重拾以往的目标,再次把帝国教育引入中小学及大众教育当中。为此,1918年6月25日,“帝国研究委员会”代表前往英国教育委员会,期望后者能在普及帝国教育的过程里发挥主持功能。主要代表布赖斯勋爵出于培养学生帝国情感的目的,希望全英国各级学校均开设英帝国历史与地理的课程。其他代表也响应了布赖斯勋爵的发言,例如卢卡斯就指出,通过英帝国史的讲授,听众将意识到帝国是一个整体,它并非通过征服与剥削得来,而是建立在自由人相结合的基础上。克拉伦斯 · 马汀(Clarence Marten,1872—1948)也认为英帝国的命运与帝国情感直接相关。
20世纪初,在“帝国研究委员会”的领导下,“帝国研究运动”掀起了讨论英帝国的热潮。时人认为截至世界大战爆发,推进帝国研究是“皇家殖民协会”开展得最成功的活动。参与者指出捍卫帝国的关键就是以帝国教育来召唤民众的帝国意识,强化精神纽带。其中,“帝国研究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把帝国教育引入大学课堂,培养合乎英帝国发展需要的精英,进而在这些精英的作用下捍卫帝国。那么英帝国史书写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03
20 世纪初的英帝国史书写
英帝国史在帝国教育事业中占据核心地位。“帝国研究运动”的参与者均认为英帝国史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对象,将它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是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他们看来,英帝国史并非单纯的学术领域,而关乎学生们的帝国认识和帝国情感,因此是捍卫帝国团结的重要因素。20世纪初,众多英帝国史研究者都是“帝国研究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其历史书写也共享了运动中的种种因素,比如认可“联盟论”,显露种族中心主义和乐观主义。
首先,20世纪初的英帝国史书写将英帝国勾勒为“联盟”,指出无形的纽带才是团结的根基。此前,西利曾通过书写英帝国史,强调英帝国是一个跨越大洋的统一国家,但该阶段致力于捍卫帝国的学者大多认为帝国联邦计划难以为继,因此纷纷把希望寄托在帝国成员间的情感纽带上。他们指出在盎格鲁 — 萨克逊民族亲缘关系的基础上,英帝国即使无法完成统一,也能在无形纽带的作用下演变为兼顾自由与团结的联盟。在“帝国研究运动”发挥重要作用的英帝国史专家艾格顿,就认为未来“帝国内各散乱部分被整合为更统一的整体是很可能的”,但“这绝不意味着,这个整体需要像原来一样,采用联邦制的形式”。与艾格顿同为“(帝国研究)讲座小组委员会”成员的卢卡斯和牛顿长期致力于英帝国史研究。两人均认为帝国联邦不可行。其中,牛顿预测未来英帝国将是“大英国协”。在他们的书写中,英帝国的历史不再被描绘为英格兰成长为统一“世界国家”的历程,而是反复凸显捍卫帝国的精神,即“个人的事业心和勇气,对共同历史的骄傲,对共同的故乡与君主的忠诚”。换言之,他们不再强调有形帝国的疆域,而是注重无形帝国的纽带。
“帝国研究运动”参与者认为,在英帝国史书写中强调无形纽带的价值并不是一种外在的灌输教育。也就是说,英帝国史书写并非在编造新生事物,而是在“验证”始终潜藏在同胞心中的精神纽带,并进一步将它们召唤出来。卢卡斯认为其目的是:
增进一种关乎帝国爱国主义的亲情感,并使之与共同利益相吻合;对走向未来的年轻人来说,尽可能地分享这种伟大的情感,就能战胜恐惧。与此同时,对分布在帝国各处的公民来说,服务帝国就是保卫帝国的团结;当越来越多千里之外的帝国白人孩童开始为帝国服务,那就会有更多人将这项事业当作使命,对越来越多来母国的人来说,留在英帝国之内是值得的。
正是出于以上目的,受“帝国研究运动”影响的英帝国史书写少了西利所注重的现实主义态度,多了更能鼓舞人心的浪漫主义色彩。
Ecce Homo: A Survey of The Life and Work of Jesus Christ
(HardPress,2018)
其次,20世纪初的英帝国史书写出于捍卫帝国的目的,以浪漫主义的态度定义帝国境内的亲缘关系,其种族中心论表露无遗。尽管作为帝国教育的倡导者,吉布指出精神遗产不是建立在血缘上,因此不为不列颠人所独占,而是能成为建构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基础。但在20世纪初的帝国教育,尤其是“帝国研究运动”中,精神遗产逐渐被打上了种族中心论的烙印。在言谈中,“不列颠性”(Britishness)或“英国性”(Englishness)等词汇被频繁使用。参与者认为运动无意营造超越过往的普世性认同,而是致力于召唤业已存在于民族意识内部的情感。正如克里尚 · 库马尔(Krishan Kumar, 1942—)所言,这种回退到种族中心论,凸显统治群体民族属性的做法恰好是英帝国受到挑战、走入危机时代的表征。
在20世纪初的英帝国史书写中,英帝国史与不列颠人的历史相交织,构成一个整体。换言之,英帝国史被视为“更大的不列颠”成长的过程,它讨论的对象是不列颠人在全球的事业。因此,在英帝国史书写应该关注什么的问题上,卢卡斯指出不列颠人及其建立的政治体的历史与特质是最关键的主题。这是因为英帝国的内涵由不列颠人决定。他说道:
大不列颠是一个岛。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一点,大不列颠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拥有这样一个帝国的岛屿,虽然日本与英国相同,但是它的帝国仍然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总是告诉自己和他人,英帝国与其他帝国不同,它是独一无二的。
基于同样理由,艾格顿不关心英帝国广布亚非地区的殖民地,而注重讨论白人定居殖民地。他认为这些来自英国本土的移民之于英帝国的价值,就相当于“成千上万无名的工人在建设中世纪大教堂时所付出的努力”。另外,牛顿在伦敦大学罗德斯帝国史教授的就职演说里也指出英帝国的特性源于不列颠移民,这些人负载着宪政体制和经验,漂洋过海,因此英帝国史也就是不列颠人及其制度、文化在全球扩散的历史。由此,他认为北美殖民地和其他白人定居殖民地才是英帝国史书写的核心对象,这是因为“在之前无人居住的土地上建立起如此伟大和人口众多的共同体,其中的文化和制度都来源于母国,并与母国一道发展”。
最后,20世纪初的英帝国史书写为阐明以教育来捍卫帝国团结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着意凸显了不列颠人的优越性。检视该时期的英帝国史书写可见,不列颠英雄的传奇故事在其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它们以“提喻”的方式象征了不列颠人的优越性以及英帝国的道德伦理。在《帝国建设者》里,司佳德将英帝国建设的原则追溯到了阿尔弗雷德大帝,认为如果没有他,那么“我们的帝国将不会比其他帝国更稳固,并且也会像其他帝国一样,早早衰落”。“皇家殖民协会”创办的《团结帝国》杂志里几乎每期都刊载若干篇英雄传记,撰写者多为“帝国研究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艾格顿认为这些英雄传奇身上蕴含着不列颠人可贵的精神,若将其融入当下的英帝国团结事业,那未来将充满光明。出于该目的,他自己也撰写了一部传记,用于表彰斯坦福 · 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的伟业。在他看来,不畏艰险、勇于探索并追求帝国荣耀的莱佛士恰好是不列颠人的缩影。
“帝国研究运动”的参与者认为英帝国的历史彰显了不列颠人的优越性,帝国教育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民众通过英帝国史,意识到本民族的“天定命运”,就如卢卡斯所言,英帝国史教育是为了让学生们知道“英帝国与其他帝国不同,它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哪些地方体现了独一无二的特点呢?
其一,独一无二的优越性体现在帝国建设的非暴力上。在比较罗马帝国与英帝国的差异时,卢卡斯认为前者的建设基于军事强制,是一个征服帝国;后者则是移民以自发形式连接而成,是一个温和且顺应自然的帝国,因此英帝国制度和文化都显露出灵活自由的特点。同样,艾格顿在讨论17世纪欧洲殖民扩张时,认为英帝国与西班牙、葡萄牙帝国不同,它是以非暴力和渐进的方式扩展势力范围,因此其主力不是军队,而是移民。另外,牛顿也指出透过英帝国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列颠人的正义、守序和热爱和平的精神。
其二,独一无二的优越性体现在帝国制度所展现出来的“自由”精神上。此阶段中,英帝国史书写强调不列颠人热爱自由的民族性塑造了英帝国的特质,这使它一方面保障了治下民众的自由权,另一方面也能维护世界的自由。卢卡斯指出无论在北美,还是在西非塞拉利昂,随着殖民扩张,英帝国将“自由”带到了当地,诸如大卫 · 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这样的传教士和探险家也致力于传播自由理念。对此,他写道:“这其中哪有什么增殖财富的贪婪念头?”这方面的观点在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得更加明显。为了与德意志帝国进行“舆论战”,英帝国史研究者将德意志帝国塑造为“他者”,认为自由精神在该国“军国主义”政治与文化的影响下必定受到压抑。相比之下,英帝国是自由的化身,也是帝国家族中的“道德表率”。1914年,艾格顿在《战争与英国自治领地》与《英帝国是抢夺来的吗?》中就说道,相比德意志帝国浓重的军国主义色彩,不列颠人在建设英帝国时始终秉持自由与公正的原则。世界大战结束后,以上思考一度变得更具影响力。学者们认为德意志帝国之所以被打败,世界之所以重归和平,“都得益于英国公民及其帝国”。即使在那些关心国际合作,投身国际联盟建设的学者的笔下,种族优越性的论调也时常出现。
总之,“帝国研究运动”参与者出于捍卫帝国的目的,强调了无形纽带的重要性。他们笔下的英帝国被勾勒为盎格鲁 — 萨克逊民族拓殖的历史。因为关注种族,这些学者把视线集中在定居殖民地上,认为帝国建设的主力是移民,殖民地与母国间具有天然的亲切感,由于帝国爱国主义建立在种族根基上,所以对它的召唤理应成功。另外,在他们看来,英帝国的建立具有非暴力色彩,而自由与和平的特质则使它能成为世界秩序的维护者。这些英帝国史研究者认为借助如上所述的历史书写,英帝国将在教育事业的开展下得到捍卫。
04
余论
英帝国史书写是帝国教育,尤其是“帝国研究运动”的核心内容,它们的目的归结为一点,即在地缘政治与英帝国团结方案变动的环境中捍卫英帝国。但随着20世纪的战争频发与殖民地解放,捍卫英帝国的事业终告失效。但在20世纪初“帝国研究运动”与英帝国史书写中得到凸显的种族特殊论和优越论却并未与现实中的帝国一道归入历史,而是始终留存在舆论空间当中。20世纪末,它们进入了“盎格鲁文化圈”(Anglosphere)的概念当中。
“盎格鲁文化圈”概念于1995年首次出现。在围绕着它的议论中,有关不列颠人优越性的论调随处可见,比如认为“盎格鲁文化圈”内的国家同文同种,共享了自由市场经济、普通法、议会民主制、清教主义等因素,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力,塑造了现今的文明形态。“盎格鲁文化圈”概念在英国保守党内颇受欢迎,现任英国首相鲍里斯 · 约翰逊(Boris Johnson, 1964— ),以及迈克尔 · 戈夫(Michael Gove, 1967— )和丹尼尔 · 汉南(Daniel Hannan, 1971— )都是它的支持者。戈夫在担任教育大臣时推行过一场“国家课程”(national curriculum)改革,其中牵扯到历史学课纲的修订。在新课纲中,英帝国的历史再次被当作增强民族认同感,提升学生爱国主义的载体。此外,以上议论也潜伏在英国“脱欧”的社会舆论内。在前首相特蕾莎 · 梅(Theresa May,1956— )的“脱欧”讲话背后就隐含着一种强调盎格鲁 — 萨克逊人特殊优越性的观点。
The Growth of British Police ... Second Edition
(British Library, Historical Print Editions, 2018)
20世纪初的“帝国研究运动”为推进帝国教育,生产出大量凸显帝国荣耀,强调不列颠人优越性的言论、观点与意识形态。同时,借助英帝国史的书写,它们成为英国人历史认识的一部分。基于此,在认识当下英国的社会氛围,分析如今英国人的身份认同及其对英国未来的看法时,我们仍有必要回顾20世纪初的“帝国研究运动”,以及受其影响的英帝国史书写,去分析那些旨在塑造英帝国无形精神纽带的种种努力。
 西服定制一般都多少钱(西服定制十大品牌)
西服定制一般都多少钱(西服定制十大品牌)
 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明细)
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房屋拆迁补偿标准明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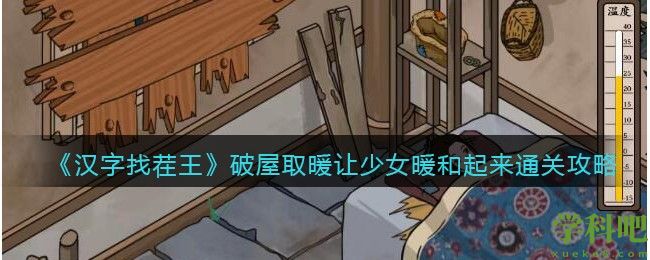 破屋取暖让少女暖和起来怎么过 汉字找茬王破屋取暖让少女暖和起来通关攻略
破屋取暖让少女暖和起来怎么过 汉字找茬王破屋取暖让少女暖和起来通关攻略
 怀孕初期症状有哪些(怀孕初期症状有哪些1-3天)
怀孕初期症状有哪些(怀孕初期症状有哪些1-3天)
 bmgbmgbmg多毛可以约线下见面?女主播:礼物刷够就行!
bmgbmgbmg多毛可以约线下见面?女主播:礼物刷够就行!
 老师家里没人你用点力好好快(老师在家待的都被嫌弃了)
老师家里没人你用点力好好快(老师在家待的都被嫌弃了)
老师家里没人你用点力好好快,没想到私底下老师这么开放。这一夜真的好爽、好刺激,没想...
 修仙自由度高的游戏有哪些 2023高人气修仙游戏盘点
修仙自由度高的游戏有哪些 2023高人气修仙游戏盘点
修仙自由度高的游戏有哪些 2023高人气修仙游戏盘点本期带来的是一些好玩的修仙自由度高...
 app福引导网站welcome被主播泄露,讲道理,功能真的太丰富了!
app福引导网站welcome被主播泄露,讲道理,功能真的太丰富了!
每天app福引导网站welcome这里都有大量的美女视频资源更新,国内的国外的全都有,为所有...
 双减政策指什么(双减政策指什么一二年级)
双减政策指什么(双减政策指什么一二年级)
双减政策指什么?各大教育机构不断在向整个社会贩卖“焦虑”,导致各家庭和学生深受其害...
 一二三四在线播放视频国语
一二三四在线播放视频国语
一二三四在线播放视频国语!今日为大家带来的一二三四在线播放视频国语是目前十足流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