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陆胤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梁启超《新史学》20世纪初,梁启超掀起震骇一时的“新史学”风潮,不仅让中国史学本身获得其近代化的新面目,更因为史学贯通古今中西的特点,在西洋
文/陆胤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梁启超《新史学》
20世纪初,梁启超掀起震骇一时的“新史学”风潮,不仅让中国史学本身获得其近代化的新面目,更因为史学贯通古今中西的特点,在西洋器物、制度、学科分类涌入,传统经学、理学、词章之学相继式微的语境下,使“史学新旧”成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与知识方法更新的重要关节。其所裹挟的社会进化论、地理决定论、人种优劣论、历史阶段论、历史因果律等观念,更是发挥了强大的“溢出效应”,影响到此后中国学术的整体走向,甚至凝结为国人面对历史与传统的思维定式。《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地理大势论》三篇,堪称梁启超“新史学”论述的核心文本;同时开始撰作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作为“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 [1],则可视为“新史学”理念的一次成功尝试。
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都不会凭空发生,总有来自内、外种种因缘的触发。学界对于梁启超“新史学”外来资源已积累了颇多考索成果。 “新史学”于清季风行一时,得到朝野上下的诸多回应。这固然要归功于新兴报章和“言论界巨子”梁启超的首倡,离不开清末趋新学人的知识氛围,尤其是当时新学界对于国家观念和社会进化论的普遍推崇;但另一方面,今文经学关于《春秋》“事”“义”关系的持续思考,晚清公羊学以“三世”之说附会西学的尝试,作为梁氏新史学背后的经学师承,更充当了接引外来资源和相关理论的中间媒介。
作为“新史学”核心文本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地理大势论》,最初都是刊登在报刊上的“觉世之文”。 晚清时代,梁启超一派维新言论获得莫大势力,有赖于其对新媒体资源的掌控,更离不开梁氏本人对报章文体的经营。因此,有必要将此数篇史论还原到最初发表的语境,从中提取其要义。
《中国史叙论》初刊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廿一日、八月初一日出版的横滨《清议报》第90、91册,纳入“本馆论说”栏目。《清议报》是戊戌政变以后康、梁一派的政治喉舌,同时带有一定的学术普及功能,旨在“增长支那人之学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继而提出“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两大主义。 [2]不难设想,《清议报》的政治与学术两方面,完全有可能在同一刊物的文本空间内互相影响。在戊戌维新失败、流亡异国的情境下, 梁启超毅然发起“新史学”,除了受到西洋和日本社会学说和“文明史论”的直接启悟(详后文),亦受制于近代国家观念勃发期的政论环境。
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于1898年12月23日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旬刊
翻阅《中国史叙论》发表前后《清议报》的“本馆论说”栏,便可从中追溯国家思潮兴起的脉络。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清议报》刊出梁启超的《爱国论》,以欧阳修《伶官传序》式的笔调发端,系统介绍对晚清人而言相当新鲜的“爱国”概念:“国之存亡,种种盛衰,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彼东西之国何以浡然日兴?我支那何以薾然日危?彼其国民,以国为己之国,以国事为己事,以国权为己权,以国耻为己耻,以国荣为己荣。我之国民,以国为君相之国,其事其权,其荣其耻,皆视为度外之事。呜呼!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3]根据中外学者考证,这一时期梁启超接受国家思想,主要是以日译本为中介,吸取了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 K. Bluntschili, 1808-1881)的观点。 [4]正是在国家学理念指引下,梁启超开始区分“君相之国”与国、民合一的现代国家,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际的《中国积弱渊源论》当中,提出“国家”与“朝廷”的区别:
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曾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国人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之耻,更何如也? [5]
从政治论说延伸到对《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之旧史学”的批判,类似观点在戊戌以前已经有所萌发,而在此时更得到了近代国家观念的充实。 须知区分“朝廷”与“国家”、“君史”与“民史”、“一人一家之谱牒”与“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6],正是“新史学”之所以为“新”的首要特征。梁启超后来将改造旧史的运动命名为“史界革命”,多半是就此政治意义而言。他极言危论道:“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7]
《中国史叙论》原是梁启超拟想中“中国通史”所的导论。所谓“中国史”,不同于以往采取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体裁的传统史著,而应是一部西式通史。正如周予同后来指出的:“通史”有古、今两种涵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这种体裁不是中国所固有,就我个人现在所得的材料而言,似乎也不是直接由西洋输入,而是由日本间接的输入” [8]。梁氏改造“中国史”的宏图,正是在这种“由日本间接的输入”的新型“通史”体例下展开。
《中国史叙论》全文共分八节:
第一节“史之界说”,阐述历史定义及范围,强调新、旧史学的区别,突出了历史因果律的观念。梁氏指出:“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从这种系统化的史观出发,即便说中国此前“无史”,亦不为过。关于史学的范围,梁启超引用德国哲学家埃猛埒济(Rudolf Hermann Lotze, 1817-1881)的说法,指出史学应涵盖智力、产业、美术、宗教、政治等领域。其中,“智力”、“美术”是需要用小注说明的新名词,“宗教”亦为梁启超新近引进的概念。此节梁启超在借用日人《史学通论》、《西洋上古史·叙论》等材料阐发新史观的同时(详后文),亦展现了全新的知识分类视野。
第二节“中国史之范围”,引入“世界史”、“东洋史”(梁氏译为“泰东史”)等当时日本流行的史学门类,暗示新史学在近代学科框架中的自我定位。梁氏指出 ,中国史作为“泰东史”的原动力,本也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但由于国势衰弱,“近来中国史之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而运用“文明史”的新视角,梁启超首先援引了西人所论的世界文明五大起源,继而指出虽然近世“泰西文明”左右世界,“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原注:即中国文明)相会合之时代”。此论呼应明治中后期日本舆论界盛行的“东西两文明结合论”,亦预示了梁启超后来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总论》中倡导的“两文明结婚”之说。此处使用的“文明”一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教昌明”,而是作为civilization的翻译语,从明治时代的日本逆输入的“新汉语”。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九〇四年《新民丛报》
第三节“中国史之命名”,解释“中国”称谓,最能呼应新史学发端前后的新国家观念的勃发。出于“尊重国民”的宗旨,梁启超不拟采用夏、汉、唐等朝代名来代指;根据“名从主人”的公理,又不欲旁采“震旦”、“支那”等外人的称呼;至于“中华”之称,又未免“自尊自大,遗讥旁观”。最后选择了人们口头习惯的“中国”一词,“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这自然是国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论述。在第六节论“纪年”时,梁启超更率先运用了“国粹”一词。“新史学”在近代国家观念输入过程中的作用,值得唤起更多重视。
第四节“地势”,在铺叙中国山川、河流大势的基础上,强调“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所最当留意也。”据近年来学者考证,这部分论述乃是综合多种日人“文明史”、“东洋史”著作而成。
第五节“人种”,主要论述中国史范围内“最著明有关系”的苗、汉、图伯特(藏)、蒙古、匈奴、通古斯六大族。晚清新学中人好言“种界”,但梁氏此处所论,却对“西人闇于东方情实”而划分黄种人为蒙古种的说法表示怀疑;又指出“今欲确指某族某种之分略线,其事盖不易易”,只能“于难定中强定之”。不妨推论,此时梁启超在接受国家观念的前提下,对种族之说不无保留。这与一年后《新民说》、《新史学》盛论“人种优劣”的立场有所不同,却能勾连到后来与革命派论战时关于“中华民族”构成的论点。
第六节“纪年”,则是延续戊戌时期观点,主张在史著中采用孔子纪年。晚清康梁一派提倡“孔子纪年”,可追溯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创刊于上海的《强学报》,当时产生了《孔子纪年说》、《纪年公理》等文。 [9]此类主张不无“改正朔”的嫌疑,随即遭到张之洞、汪康年等稳健派的反弹。在与其师讨论《时务报》是否采用孔子纪年时,梁启超本人亦持保留意见。 [10]《中国史叙论》此节,则是从史学本身的需要来讨论“纪年”问题。 梁启超指出纪年不过“历史之符号”,却有“文明”、“野蛮”之分,应以“其符号能划一以省人之脑力者为优”。针对当世流行的“耶稣纪年”、“黄帝纪年”之说,梁氏强调“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故援耶教、回教之例,以孔子为纪,似可为至当不易之公典”。
第七节“史以前之时代”,主要借用19世纪欧洲考古学关于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分期说,结合西方社会学划分酋长时期、豪族时期、君主专制时期的论述,来推测中国史前的时代区划和阶级分化。
第八节“时代之区分”,阐述梁氏设想的中国史分期,最能体现“通史”这一外来史学体裁的特点。虽已意识到“时代与时代,相续者也,历史者无间断者也。人间社会之事变,必有终始因果之关系,故于其间若欲划然分一界线,如两国之定界约焉,此实理势之所不许也”, 梁启超仍采用了西洋史划为“上古”、“中古”、“近世”的三阶段,并以之与中国史地理范围的扩充相配。“上世史”由黄帝到秦始皇一统,乃中国民族自相竞争团结的时代,称为“中国之中国”;“中世史”由秦一统直至清乾隆末年,乃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竞争之时代,称为“亚洲之中国”;“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迄今,称为“世界之中国”。就其中“中世史”时代太长的问题,梁启超解释道:“中国以地太大、民族太大之故,故其运动进步,常甚迟缓,二千年来,未尝受亚洲以外大别种族之刺激,故历久而无大异动也。”这正是早期传教士著作和黑格尔《历史哲学》所宣扬的中国历史停滞论。而有关近世史乃“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的论述,则显示出当时日本政界“黄白两人种竞争”说的影响。 [11]
半年以后,《清议报》停办,梁启超继而发起《新民丛报》,在“历史”栏(初为“史传”栏)刊出《新史学》,同时在“学术”栏首发《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辟“地理”栏连续发表《中国地理大势论》、《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文。“历史”、“地理”、“学术”等栏目的细化,标志着梁启超等《新民丛报》编者学科观念的成熟。 就文本而言,《新史学》与《中国地理大势论》两篇,可视为此前《中国史叙论》的框架的放大和具体化;其间不无章节内容的补充,也不排除个别视点的游移。
1904年《饮冰室文集类编》所载《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改题《中国史界革命案》
《新史学》成型的部分,包括“中国之旧史学”、“史学之界说”两章正文,以及《论正统(悬谈一)》、《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续悬谈一)》、《论书法(悬谈二)》、《论纪年(悬谈三)》四篇“悬谈”。梁启超曾在“史学之界说”章末自陈:“作者初研究史学,见地极浅,自觉其界说尚有未尽未安者,视吾学他日之进化,乃补正之。” [12]可知在梁氏心目中,《新史学》还是未定稿。而《论正统》篇首又有识语云:“《新史学》本自为一书,首尾完具,著者胸中颇有结构,但限于时日不能依次撰述,故有触即书,先为散篇,其最录之,俟诸异日。” [13]然则,梁氏本应计划有一种关于史学通论的完整著作,而今日所见,仅为其一部分,所谓“散篇”即四篇“悬谈”。正文第二章与“悬谈”第一篇的发表相隔四个月。似可由此推断,梁启超本拟按照其理想中的著述结构“依次撰述”,但前两章完成后,《新史学》的著作工程便停顿了下来,最后只能以散篇的形式零星表露其观点。
第一章“中国之旧史学”,仍是在近代欧洲国家思想发达的对照下,反衬中国旧史学的简陋无用。 梁启超主张,史学应是“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甚至说“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取此与传统目录学所列正史、编年、记事本末等十类旧史相对照, 旧史观的四大弊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遂昭然若揭。由此延伸出“史裁”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此章继承了戊戌以前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共同提倡“民史”的成果(所以才说“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又吸收了从《清议报》时期国家主义论说到同时期《新民说》所涵盖的若干新知,如朝廷国家、个人群体之辨等。故其资源并非局限于史学,影响亦更蔓延到史学以外。梁启超指出中国旧史书读不胜读,导致治中国史学无从下手,是由于缺少一部“善别裁之良史”;又强调中国史籍“难读”、“难别择”、“无感触”三项缺点。其实这些批评,都可挪用到史学以外的领域。趋新姿态的背后,则是要求读书方法的变化:从读《二十四史》、《九通》、《通鉴》等原典,到读分章析节的西式通史、通论、教科书。潜移默化之间,梁启超以新史观改造国人知识生活,作用实为巨大而深远。
当然,梁启超对中国旧史学亦非全部抹杀,他列举二千年来史家稍有创造者,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六家。尤其突出黄宗羲创作“学史”之功:“使后人能师其意,则中国文学史可作也,中国种族史可作也,中国财富史可作也,中国宗教史可作也。”说明 扩展史学领域,开辟学术史的新途,早已有本土资源可供利用。
第二章“史学之界说”,多直接搬用日本学者讲义录内容,引进空间/时间、天然/历史、客观/主观等对立范畴,强调新史学所应具备的进化视野、群体意识和求得“公理公例”的本质追求;并进一步要求扩展史学范围:从客观对象上,“内自乡邑之法团,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均须尽力扩展史料;而在主观凭借的方面,则应注意史学与他学之关系,吸收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经济学),以及其他哲学、文章学及自然科学等各科知识。
到了“悬谈”四篇,史学论述背后的政论色彩进一步凸显。 《论正统》强调“民统”驳斥“君统”,大量取用王夫之《读通鉴论》的相关论述,在继续发挥戊戌时期“民史”观念的同时,更有张扬英、德、日一系君主立宪政治的用意:“英、德、日本等立宪君主之国,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若是者,其犹不谬于‘得邱民为天子’之义,而于正统,庶几乎近矣。”实际上是借史学问题抒发立宪政治的观念。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篇,看似承袭《中国史叙论》的“人种”一节,实则范围大为不同。《叙论》专论中国史范围内的“种族”(相当于今天的“民族”概念),而《新史学》此篇则主要讨论黄、白、黑各人种及其内部各支系的竞争升降。梁启超引进了“历史的”与“非历史的”人种、“世界的”与“非世界的”人种等对立概念,含有比较优劣的意味。在同时期所撰《新民说》的《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一篇中,梁启超就曾断论:“由此观之,则世界上最优胜之民族可以知矣。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人最优。此非吾趋势利之言也,天演界无可逃避之公例,实如是也。” [14]到《新史学》中,梁启超借用日本“文明史”著作为材料,全面论证白种阿利安人种的条顿人,“实今世史上独一无二之主人翁也”。从而在全新的意义上,确立了“世界文明史”的“正统”。故此篇初刊于《新民丛报》时,便是以《论正统》的续篇(“续悬谈一”)面目出现的。
清乾隆武英殿刻《二十四史》
《论书法》篇指斥传统史家以《春秋》书法为褒贬的谬误。梁启超借用《公羊》经学的《春秋》观,在经与史、明义与记事之间作出划分,指出:“《春秋》之书法,非所以褒贬也。夫古人往矣,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孔子岂其不惮烦,而一一取而褒贬之?《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以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识焉以代之。……惟《春秋》可以有书法。《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记事也。使《春秋》而史也,则天下不完全无条理之史,孰有过于《春秋》者乎?”然而,梁启超并没有完全否定史家“书法”。他特别在篇末表彰了普鲁塔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以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更推崇吉本《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 西式评传体裁的引进,是“新史学”同时期梁启超的另一史学贡献;而学者正可从全新的“书法”追求当中,读出梁启超“史界革命”的文体理想。[15]
《论纪年》篇基本上延续了《中国史叙论》的相关材料和观点,惟突出传统纪年体现的“正闰”问题,将之列为批判对象,则可视为《论正统》一篇的延续。
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至五月,梁启超断续三次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地理大势论》,亦可看作是《新史学》的篇外“悬谈”。关于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同时期梁氏还先后撰有《亚洲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篇章,多直接采译日本“文明史”著作;而《中国地理大势论》则是梁启超原创的论文。全篇从政治、学术、风俗、兵事四方面阐述中国各区域地势与历史演进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文中收有《黄河流域国都表》、《扬子江流域国都表》、《历代革命军及割据国所凭借地理表》,初步运用了数据统计的方法。
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的“中国地学会”及其创办的《地学杂志》
以《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地理大势论》等篇为代表,梁启超掀起的“史界革命”风潮在清末的新知识界引起了广泛回应。比如光绪二十八年创刊于上海的《政艺通报》,原仅按“政学”、“艺学”分为上下编,至当年七月第12期发刊,增加中编“史学”,先后刊出邓实《史学通论》、马叙伦《史界大同说》等文。同年八月发刊的《新世界学报》,亦多有马叙伦等人呼应梁派“新史学”的文字。凡此,均可视作受到“新史学”风潮的鼓舞。 以这两份刊物为媒介,“新史学”甚至超越了政治畛域,对晚清国粹派学人及其学术的展开,亦有深远影响。
清末“新史学”的发皇,离不开外来资源的刺激,而以梁启超新史学著作的取材为中心,又可分为两个关键时段:一是丁酉、戊戌(1897-1898)前后的酝酿期,梁启超等人直接吸收西方社会学史论,初步形成其“民史”立场,提出扩大史学范围的诉求。其时,如夏曾佑、唐才常、谭嗣同等梁氏论学的同道,都曾致力于提倡“民史”,吸取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对旧史进行批判。二是辛丑、壬寅(1901-1902)前后“新史学”著述形成时期,主要是取用来自明治日本的“文明史论”,将既有的“民史”观条理化,形成关于“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历史与地理”关系的具体论述。
梁启超改造旧史学的论说,可以追溯到戊戌维新以前。在光绪二十三年发表的《变法通议·论译书》篇中,梁氏就提出了“君史”与“民史”对立的观点:
史者,所以通知古今,国之鉴也。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原注:谓格致等新理)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言其新政者,《十九世纪史》等,撰纪之家,不一而足,择要广译,以观西人变法之始,情状若何,亦所谓借他人之阅历而用之也。 [16]
同年三月,唐才常、谭嗣同等主办的《湘学新报》出刊,首列“史学”栏,同样张扬“民史”的新观念。正是在“外史”广阔领域的对照下,谭嗣同随后才把中国传统的《二十四史》概括为“一姓之谱牒”。 [17]梁、谭、唐等“民史”观的发端,很可能是以教会系统译印西书为中介,直接汲取了19世纪英国社会学者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相关论述。
斯宾塞《教育论四篇》(Four Essays on Education)中《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一文,在光绪八年(1882)由颜永京译出,题为《肄业要览》。梁启超《西学书目表》(1896)将此译本归入学制类,称其“有新理新法”;继而又在《读西学书法》(1896)中提到“颜永京有《肄业要览》一书,言教学童之理法,颇多精义。父兄欲成就其子弟,不可不读之 ”[18],可谓推崇备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肄业要览》收入梁启超主编的《西政丛书》。同一译本又在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初一日至次年二月初一日间,以《史氏新学记》为题,连载于唐才常、谭嗣同主办的《湘学新报》第8至28册。
Herbert Spencer(1820-1903)
在该文中,斯宾塞主张以一种功利价值观来划分知识等级,提倡科学实用,反对古典语文教育;具体到历史学,则认为“史学与别物无异,终以有济实用为定”,并提出著名的“邻猫生子”比喻。 [19]当时《湘学新报》的编者,曾敏锐地看出斯宾塞与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篇持论的共同点。 [20]而关于“君史”、“民史”的对立,以及如何扩充史学的范围,最可能打动梁启超等人的,应是如下一段议论:
古时列国皆以国王为注意,下此臣民,无足轻重。所以作史者但记君上之事迹,而于民间之风土人情缺焉不讲。夫 史记中于人最有关涉者系草野中事。是以作史者宜备载国之如何缔造、如何坚立,国内有何等民,其行政与治民之法何若,有何偏见、有何弊病,以及四野之情形,国中有何教,其教有何法度、有何权柄、有何仪节、有何经典,信从者或情愿或勉强,于国家有何损益;宜备载民间有何等称谓,有何交接之礼,上下间往来有何文法,盖观此可以见上下之相视相待;又处家处外之风俗规矩,以及父子夫妇两伦之次序,彼此相视之大概;民间之蛊惑,如异端之符术怪诞,世俗之拘忌,小孩所佩带之压邪诸器物;载明国内有何项之生计,一人专攻一艺或兼营别业,耕田制物有何等之机器,所制之物精粗何若,货物以何而广运,贸易用何等之银钱,行业有何世守,各业有何行规。史记亦宜备载肄业之情形,即如小孩读何种书,诵习几何年,有何格致之学,时世之趋向,民间之思议,儒士有何立论,房屋款式、衣冠、雕刻、字画、音乐、诗赋、稗乘,以见民之雅俗、饮食之物、玩戏之事;居家若何过度,有何自怡之境,国内之律例,民间之习气,一切举动俗语,以觇其德行之大凡。予以似此之史记,自有大用,读之者由此而知为人之方。
斯宾塞指出,历史学要“有济实用”,便不能由“君上之事迹”来主导,而应关注最有关系的“草野中事”,包括政治、法律、宗教、礼节、风俗伦理、民间信仰、经济贸易、行业制造、教育学术、建筑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部分论点似已预见到20世纪新文化史或文化研究的取向。 梁启超对于“中国之旧史学”的批判,容易给人“西史”整体进步印象。而从斯宾塞对当世“作史者”的描述却可看出,当时西方史学本身仍处在从“君史”到“民史”的演化进程中。戊戌以前梁启超等接触到的浸润着功利论、社会进化论的史学观,并不能涵盖19世纪欧洲史学的整体。
然而,正是这种带有浓厚社会学色彩的新史观,却在19世纪后半近代转型期的东亚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参与构建了近代东亚认知框架的重组。 在这方面,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日本。而其传输媒介,则是同样有着社会进化论背景的“文明史学”。作为Civilization译语的“文明”又译“开化”,幕末到明治初年,以基佐(F. P. G. Guizot, 1787-1874)、巴克尔(H. T. Buckle, 1821-1862)等人著作为中介,由西周(1829-1897)、福泽谕吉(1835-1901)等启蒙思想家引进,并经田口卯吉(1855-1905)结合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说,确定为一种历史评判的标准——“文明”只属于欧洲,是一单线历程;对尚处“半开”的东亚而言,“文明”是进化历史的前景,有待完成的将来。 [21]作为著述体例的“文明史体”有三大法则:(一)进步的观念,(二)因果律,(三)向着“文明”或“人民”的全体扩充历史的范围。 [22]在被认为是“紊乱”、“无条理”、“欠分科”的东亚传统学问重组为近代学科(哲、史、文)的过程中,以上“法则”影响深远。
一时间,“谈史则曰勃克尔,论社会法则曰斯边撒” [23],文明论结合社会进化论,逐渐沉淀为明治时代日本受教育阶层的常识,亦由此意识到本国旧史学的缺陷。如近代日本的启蒙先驱福泽谕吉,就在其影响巨大的《文明论之概略》(1875)一书中指出:
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多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像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情况。就是偶尔涉及与政府无关的事,无非是记载一些有关佛教的荒诞之说,是不值得一看的。总而言之, 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 这是由于学者的疏忽,可以说是国家的一大缺点。 [24]
福泽谕吉(1835 -1901)
不难发现,福泽谕吉采取了与斯宾塞完全相同的论调;所谓“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之说,正可视作梁启超《新史学》中“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说法的直接来源。到明治中期,属于学院派史学的高津锹三郎(1864-1921)描述当世史学的状况:“我国古来之学科,近来改变其面貌最甚者,当系史学。……随着西方学术之盛行,以致史学目的和历史体裁皆为之一变。” [25]这也让人想起梁启超《新史学》劈头而来的那句话:“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
1929年,梁启超辞世不久,就有人提到:“梁氏最著名之《新史学》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多以日人所著为蓝本。” [26]梁启超对明治日本“文明史”著作多有搬用,不少地方甚至是直接的抄译。这一影响关系,近年来已经日益为学界所认识。梁氏“新史学”相关著述材料的具体来源,略如下表所示:
* 本表利用了以下先行研究:
(a)蒋俊《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文史哲》1993年第5期。
(b)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5-119页。
(c)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
(d)邬国义《梁启超新史学思想探源》,载浮田和民讲述、李浩生等译、邬国义编校《浮田和民〈史学通论〉四种合刊》卷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梁启超新史学著述的直接材源,多为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的讲义录。事实上,占据学院主流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史学早在1880年代末,就由任教于帝国大学(东京)的兰克弟子利斯(Ludwig Riess, 1861-1928)引进了。但梁启超却选择了流行于民间或讲坛的“文明史学”,与学院派的兰克史学保持距离。这或许可以从梁氏自身的著述风格与知识背景来解释。“文明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常与报章政论相结合,带有文明批判的性质;在文体上则多采用史论体,“所重者在论断而不在事实,故其所记载,惟择其有关于议论者而录之”。 [27]这吻合梁氏的报馆经历与行文风格。 更重要的是,文明史学所櫽括的斯宾塞一派社会进化学说,梁启超在早年已经有所接受。
梁启超到日本后,以福泽谕吉文明论为中介,接受了文明史学的观念。而此时,日本的文明论和文明史学,已经完成从民权主义、平权论向帝国主义、强权论的转型。《新史学》的主要材源之一浮田和民(1859-1946,时任东京专门学校讲师),便是帝国主义论的热忱宣传者。 [28]强权论立论的基础仍为社会进化论。[29]因此,带有民族竞争、强权论甚至种族论倾向的《新史学》,仍可看作是对斯宾塞一派社会学说的演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起,梁启超主导的《清议报》连载了日本社会学者有贺长雄(1860-1921)的《社会进化论》。这是一部“基本忠实地抄袭了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的著作。论及社会学“功用”时,有贺氏批评未有社会学之前的历史,不是“以国家之事变,全归于君主一身之所作为”,就是“只论一种数种之事变,不涉社会中各种之事变”,指出如果没有社会学提供的“普通进化之理”,则“历史甚难造作”。在有贺长雄看来,斯宾塞的“社会进化之理,理原一贯,无东西之别,苟知其一,据此可知各国进化之大体”,甚至能推断“无口碑文献时代”的变迁。 [30]凡此种种,都可用来诠释《新史学》以社会进化论改造旧史学的思路。
梁启超对“文明史学”的全面接受,还可以从与《新史学》几乎同时发表的《东籍月旦》一文中得到印证。该文提倡以阅读日文为获得新知的途径,分类评价当时日本的学术著作(包括日人所译西书)。无论就“史识”还是“史裁”而言,梁启超都难掩其对于明治日本“文明史”体裁的推崇:
文明史者,史体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颇不易,盖必能将数千年之事实,网罗于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别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论断,然后为完全之文明史。
梁启超评论日人所译基佐《欧罗巴文明史》,特指出:“基氏为文明史学家第一人。”接着介绍高山林次郎(1871-1902)《世界文明史》,更进而申言:“鄙人不揣梼昧,近有泰西通史之著。”论及白河次郎(1874-1919)、国府种德(1873-1950)合著的《支那文明史》,则进一步透露自己欲撰述中国文明史的意向:“中国为地球上文明五祖国之一,且其文明接续数千年未尝间断,此诚可以自豪者也。惟其文明进步变迁之迹,从未有叙述成史者。盖由中国人之脑质,知有朝廷不知有社会,知有权力而不知有文明也。此书乃草创之作,虽未完善,然大辂椎轮,厥意亦良善矣。” [31]对照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学》篇在朝廷与国家、个人与群体,陈迹与今务、事实与理想之间作出的分辨,可知正是“文明史”的广阔视野,接续了此前直接从斯宾塞史论启悟的“民史”观,进一步照亮了传统史学忽略的角落。
事实上,《东籍月旦》的史学部分,正可看作“新史学”的一份参考书目,其传播“史界革命”风潮的作用,并不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地理大势论》等史论之下。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光绪二十八年 (1902),王舟瑶在京师大学堂掌教“中国通史”、“学术史”课程,讲义内有《论读史法》一则云:
今之言新史者,动谓中国无史学,二十四史者,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虽过,却有原因:盖西人之史,于国政、民风、社会、宗教、学术、教育、财政、工艺,最所究心,所以推世界之进状,壮国民之志气。中国之史,重君而轻民,陈古而略今,正闰是争,无关事实,纪传累卷,有似志铭,鲜特别之精神,碍人群之进化,所以贻新学之诮,来后生之讥。学者宜自具理想,以特识读旧史,庶不为古人所愚乎? [32]
此段强调读史须有“理想”、“特识”,应在“君民”、“古今”之间作出别择,反对正闰说和纪传体,几乎是梁派“新史学”观点的笼括。王舟瑶的讲义先后列举桑原隲藏(1871-1931)著《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1873-1923)著《东邦近世史》、市村瓒次郎(1864-1947)与泷川龟太郎(1865-1946)合著《支那史》、那珂通世(1851-1908)著《支那通史》、河野通之(1842-1916)与石村贞一(1839-1919)合著《最近支那史》、田口卯吉著《支那开化小史》、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等著作,正是拜《东籍月旦》介绍之赐。不仅其所列书目与《东籍月旦》东洋史、中国史部分基本重合,就连书目下“惟以外国人而编中国史,则又病于太略,且多舛误,有志者能自为一书则善矣”的案语,亦来自梁启超“以外国人著中国史,又苦于事实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的论断。 [33]这一切,无不说明梁启超借鉴日本“文明史论”的取径,不仅在南方新学界获得巨大反响,在癸卯(1903)以前作为清廷官方教育行政中心的京师大学堂,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34]
考索清末“新史学”观念的生成,除了外来资源的启瀹,亦不能忽略本土经学师承。尤其是梁启超作为康有为弟子和晚清“今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其经学思想对于“新史学”论述的渗透,以往学界不无忽视,值得细加考论。
梁启超自称“自三十以后……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 [35]梁氏的“三十前后”,正是撰述“新史学”的时期。那么,当时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学术的分歧,是否有可能影响到梁氏新史学的构建?其实,只要细读《新史学》的文本,就会发现:在化用日本文明史著作的字里行间,读者还会时时遭遇康有为的影子。比如《论正统》篇引“通三统”来解说“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 [36],《论书法》篇主张“《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记事也” [37],都属典型的《公羊》经说。而其中最精彩的段落,还数运用“张三世”来缘饰作为《新史学》思想骨干的社会进化论:
《春秋》家言,有三统,有三世。三统者,循环之象也,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是也;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三统则非历史之情状也。三世之义,既治者则不能复乱;藉曰有小乱,而必非与前此之乱等也。 苟其一治而复一乱,则所谓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学者,当从孔子 (春秋三世)之义,不当从孟子 (一治一乱)之义。 [38]
这些细微之处,无不提示康有为所张扬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依然影响着梁启超。依据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 梁氏划分宇宙间的现象为循环和进化两种,分属于空间和时间、天然界与历史界,正好可以对应《公羊》经学“三科九旨”的“通三统”与“张三世”。梁启超指出,历史界的现象,应用“三世”进化来解释。
浮田和民(1860-1946)
“三世”之说发端于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谓“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所传闻杀其恩”,将十二世分为“三等”,原不过是对《春秋》书法“异辞”现象的一种解释。 [39]至何休《公羊解诂》提出“三科九旨”,将其中“三世”解释成“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依次递进的政治演化,辅以“新周故宋王鲁”、“通三统”、“异内外”等非常大义,遂将此问题义理化。 [40]迨清中叶,常州今文学者重新发掘“三科九旨”,稍后龚自珍《五经大义终始答问》更明确指出:“三世”不仅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时代区划,“通古今可以为三世”,乃是对于整个历史的阶段划分。 [41]然而,晚清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的“三世”观,并不单纯源于今文经学的师传。
康有为最初的今文经说注重析学辩伪,不太涉及“三科九旨”等非常大义。即便是在授业解惑时偶尔提到“三世”,也是措辞闪烁,所指并不明确。 [42]倒是游离于康门的夏曾佑,在光绪二十一年春致宋恕信中将“三科九旨”大大发挥了一番。夏氏认为孔子之教“不外三科九旨,而诸弟子有全闻者,有半闻者。全闻者知君主之后,即必有君民并主与民主,故道性善……其不全闻者,不知后二,但知初一,故言性恶而法后王。” 夏曾佑立论大旨,在于将“三世”表述成“君主→君民并主→民主”的政制进化。孔门中主性恶的荀子一派只闻前二者,孟子一派则全闻其说,“太平之世,用心也精”,所以宣扬民主、道性善。 [43]同样道理,正是因为坚信性善,才会对时间进展有完美想象,也才能接受世界将循一定阶段而日臻完善的设定。夏曾佑在孟、荀对立的框架下拓展了“三世”说,这种思路,很可能影响到当时与夏曾佑共同论学的梁启超。
康有为(1858 -1927)
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严复给梁启超寄去《天演论》原稿。 [44]此时夏曾佑正在天津候选,旋识严复,交往甚密。次年(1897)春,梁启超致信严复,称“南海先生读大箸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又云:“顷得穗卿书,言先生谓斯宾塞尔之学,视此书尤有进,闻之益垂涎不能自制。” [45]康、梁接受严复译介的社会进化论,仍有夏曾佑的作用在内。同一信中,梁启超与严复争论希腊罗马有无民主制度,也抬出了《公羊》经学的“三世”说。在梁启超的现存著述里面,这是较早将“三世”之说附会于社会进化论的例子:
《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地学家言土中层累,皆有一定,不闻花刚〔钢〕石之下有物迹层,不闻飞鼍大鸟世界以前复有人类。惟政亦尔,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有君权。 [46]
虽在细节上有所不同,梁启超对“三世”说“多君为政→一君为政→民为政”的政治阐发,明显带有夏曾佑的痕迹。更进一步,他更将“三世进化”看成是像地层排列般不容质疑的“公理”,断言希腊罗马“皆多君之世,去民主尚隔两层”。《公羊》三世说与地质考古术语结合,使梁启超的断论看上去更具权威,甚至可以不顾史实。半年以后,梁启超又在《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中把“多君→一君→民政”的三世图景细化为“三世六别”,并且强调:“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阏之……如地质学各层之石,其位次不能凌乱也。” 三世之说已然不仅仅是关于既往历史的概括,更包含着对现实政治及人类未来命运的决定力和预测力。任何对于“三世进化”框架中既定时段的阻碍或超越,都被认为是“于公理不顺,明于几何之学者,必能辨之”。[47]
同样在光绪二十三年,康有为《春秋董氏学》问世。在这部结论先行的著作中,康氏推重《公羊》三世之说“为孔子非常大义”,且将三世之分同《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相配:“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因此孔学也分“小康”、“太平”两种:“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 [48]这与前此夏曾佑、梁启超等发明孟子传大同、荀子传小康之说,思路并无二致。梁启超把“三世进化”牵扯上“几何之学”,康有为眼中“三世”、“三统”、“内外”等义例,亦如几何原理:“学算者,不通四元、借根、括弧、代数之例,则一式不可算;学《春秋》者,不知托王改制、五始、三世、内外、详略、已明不著、得端贯连、无通辞而从变、诡名实而避文,则《春秋》等于断烂朝报,不可读也。” [49]如同数学规则使计算成为可能,《春秋》义例亦使《春秋》由简陋的史料上升为宣扬微言大义的经典。
对“三世进化”的体认,大致在光绪二十三、四年之间,渐渐成为趋新知识界的潮流,这一时期正与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民史”观的发端相重合。丁酉正月,徐勤撰《地球大势公论序》指出,洪荒以来的人类历史无不循一定的“大势”而行:“始于散而终于合,始于塞而终于通,始于争而终于让。” [50]时人好将《春秋》与其幻想中旨在伸张国际正义的“公法”相类比。不仅认为万国公法“西人以比中国《春秋》,盖亦以空文垂教之作”; [51]《春秋》本身也因为具备了“爱民”、“存亡续绝”、“弭兵”、“贵自立”、“天下为公”、“有分土无分民”等义,而被认为“万国之公政,实万国之公法也”。 [52]推崇“公法”的理据,正如谭嗣同所说,乃在于确信“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不同文化背景、纷繁复杂的人事现象背后,都冥冥存在一种确定不变的义理,“是之谓公理。且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53]对西来的“公理”、“公法”的想象和本土化努力,是为了推倒目前权威,在此同时,当然也有意无意会树立新的权威。
同年三月,唐才常、谭嗣同等主办的《湘学新报》开辟“史学”栏,唐才常发表《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一文,提出“孔教微,无公理;公理微,无信史”,在史学中提倡“公理”,意在祓除旧史“言例言法、言闰言正、言道学儒林”的迷妄,求得符合《春秋》公理的“信史”。这岂不正是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论书法”,以进化论之“公理公例”掊击“中国之旧史学”的先声? [54]唐才常以为今日作史“宜以《春秋》为体,以各国百年来史乘为用”;而梁启超也在同时期多次提到西方政治学院“以公理公法之书为经,希腊罗马古史为纬”的学制,强调中国兴政治学“宜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 [55]即欲以“公理”、“公法”破除陈见,经纬古史;具体到中国,则是用经子之“义”来涵盖历朝掌故之“事”。
创办于湖南维新运动期间的《湘学报》和《湘报》
当时唐才常、梁启超、谭嗣同所说的“公理”,是“唐虞三代君民共有之权衡也。民宅于器曰公器,器周于法曰公法,法权于心曰公心,心萭于理曰公理”。公理之“公”,与君主一家之“私”相对立。今人固然容易从文化多元的立场,指摘当时人崇信“公理”实为膜拜“西理”;但若回到历史语境, 唐、梁、谭等维新志士提倡“公理”、“民史”,本意在反抗权威,祓除迷妄,更应肯定其积极面向。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学问大进,但其以公羊“三世”理解历史进化的思路却没有改变。梁启超不仅以“三世”比附福泽谕吉文明论的“文野三界之别”, [56]更在己亥四月发表的《论支那宗教改革》演讲中,称孔教为“进化主义”,并进一步明确了公羊“三世”与达尔文、斯宾塞进化论的关系,指出:“第一,孔教乃进化主义,而非保守主义。《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太平。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达尔文)、士啤生(斯宾塞)氏等所倡进化之说也。” [57]此时正值梁启超接受国家思想强权论时期,虽逐渐认识到“百卷万国公法不如几门大炮”,却依旧用“三世进化”来概括强权斗争的历史。 [58]公理之“公”,重点已不在体现民意或伸张国际正义,而被认为与残酷的生存竞争法则一样,是一种客观的、强势的现实。
《公羊》经学的“三世说”最终能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结合,在于二者都强调历史进程背后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阶段性和方向感,从而为叙述与阐释历史提供了一套有效图式。在光绪二十七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仿照日本的通史著作,挪用西洋史时代划分,将中国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期。而其创见,还在于以文化地理关系解说三期之变迁:上世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争竞自团结之时代也”;中世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近世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 [59]细按此说,实与《公羊》“三科九旨”中“异内外”(衰乱世“内其国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 [60]的框架相近。“三世”说由董仲舒《春秋繁露》最初提出,到近代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运用,其内涵流变略如下表所示:
从何休《公羊解诂》开始,“三世”就不再停留于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史,而是在一代之“事”中,寄寓了由衰乱经升平而太平的万世理想。今文家常援引司马迁转述的孔子遗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在“义”与“事”之间,“义”有绝对权威,“事”只是使“义”更加生动化(“深切著明”)的材料。故《公羊》经学的《春秋》观,并不排斥(甚至纵容)“义”与“事”的错位,隐含着用“义”抹杀“事”的可能性:“鲁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广,世愈乱而《春秋》之文益治,甚至西狩获麟于《春秋》本为灾异,而托之以为治定功成之瑞。”刘逢禄指出,“《春秋》之义,犹六书之叚借,说《诗》之断章取义。……愀然以身任万世之权,灼然以二百四十二年,著万世之治。” [61]梁启超《读春秋界说》也指明:“《春秋》本以义为主,然必托事以明义,则其义愈切著。”《春秋》不是史,而是象征之书、记号之书,“读《春秋》当如读《楚辞》,其辞则美人芳草,其心则灵修也,其辞则齐桓、晋文,其义则素王制也”。 [62]因此,康梁一派等在言及历史问题时,也往往以经视史,强调“经义”、“史裁”,到梁启超的《新史学》中,对旧史的批评于是就主要着眼于史观(“四弊”)、史裁(“二病”)两方面。
是之谓“借事明义”,或者按照后来皮锡瑞的解释:“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 [63]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推论“有史以前之时代”,引进19世纪中叶欧洲地质考察的分期结论(石刀期→铜刀期→铁刀期),用之推论中国的史前历史:
中国虽学术未盛,在下之层石,未经发见。然物质上之公例,无论何地,皆不可逃者也。故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史前之史,决不为过! [64]
他方考古所得“公理公例”,无须证明便可挪用于中国。而本土史家的义务,则为“按世界进化之大理原则,证之于过去确实之事,以引导国民之精神” [65]。史实固然要确实,但目的还在于疏解业已被证成的“大理原则”。 总之,梁启超早年史学受公羊家“借事明义”说的濡染,主要在“义”的领域深耕,其意义更在于引进一种新观念(进化论),用国人熟知的史实解释、旁证之,以裨国民精神之进步。《公羊》经学的“三世说”在晚清新知识界相当流行,即便学术路径或政治主张与康、梁等不甚契合者,如章太炎、孙宝瑄、刘师培辈,都曾一度认同, [66]则其对于近代学术思维的影响,自不可小视。
百馀年来,梁启超“新史学”对于现代中国史学乃至整个知识、学科转型的意义日益凸显,其所流露的政治意识与外来资源,得到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认同和发掘。今人较易理解清末“史界革命”启瀹民智、扩展学科边界、开拓知识方法的意义,却对其系统化论述背后的经学观点和学派预设有所忽略。
梁启超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
在学科编制与启蒙心态日益成为反思对象的今天,理解清末“新史学”的成就,似乎不应再满足于抽象地继承梁启超过于条理化、政论化的结论,更不必认可其所援引的人种优劣论、地理决定论、社会进化论等带有19世纪偏见的论述框架。 重要的是,如何把“新史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来观照?我们或可关注学术文本在政治语境中形成的过程,从而梳理学术流变的内、外因素;与此同时,亦不妨回到以个人为中心的“旧史学”视野,采用被梁启超唾弃的“铺叙”法,回放学派分合的情境,追溯学术文本生成与流转的途径,达成具体人物知识视野的贯通。梁启超本人的史学观念,在民国以后尚多有变数,但其对思想界发挥最大影响的时期,却仍是在清末。若考虑“民史”、“文明史”、“三世进化”与唯物史观及其历史阶段论的关系,则相关问题的反思,尚有向下延伸的馀地。
2012年12月12日写于北大图书馆
本文收入《变风变雅:清季民初的诗文、学术与政教》,陆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夏晓虹《中国学术史上的垂范之作——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 《横滨清议报叙例》、《本报改订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1册,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十一日、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初一日。
[3] 哀时客(梁启超)《爱国论一》,《清议报》第6册,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一日。
[4] 巴斯蒂(M. Bastid)《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狭间直树《梁启超研究与“日本”》,《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24期,1997年9月。
[5] 梁启超《中国近十年史论·积弱渊源论》,《清议报》第77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十一日。
[6] 任公(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清议报》第90册,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廿一日。
[7]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第一章 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第1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一日。
[8] 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四辑,1941年2月。
[9] 关于康有为等人采用“孔子纪年”的考释,参见村田雄二郎《康有为与“孔子纪年”》,王晓秋主编《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的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09-522页。
[10] 梁启超《与康有为书》,原载《觉迷要录》卷四,引自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11] 近卫笃麿《同人种同盟 附支那问题研究の必要》,《太阳》第4卷第1号,1898年1月1日。
[12]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二·第二章 史学之界说》,《新民丛报》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13]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三·论正统(悬谈一)》,《新民丛报》第11号,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14] 《新民丛报》第2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
[15] 参见陈平原《“元气淋漓”与“绝大文字”——梁启超及“史界革命”的另一面》,《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16] 《时务报》第27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廿一日。
[17] 谭嗣同《湘报后叙》,《湘报》第11号,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
[18] 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2、1164页。
[19] 史本守(Herbert Spencer)著、颜永京译《肄业要览》,《西政丛书》石印本,第12a-13a页。
[20] 《掌故书目提要·肄业要览一卷》,见《湘学新报》第4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21] 如福泽谕吉在《文明论之概略》中有“日本文明的来源”一章,提出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日本文明”,但其特点是“偏向于权力”,长期停滞,事实上并不具备欧洲意义上“文明”的性质,因此在“文野三界之别”(野蛮—半开—文明)中只属于“半开”。
[22] 参考小泽荣一《近代日本史学史の研究——19世纪日本启蒙史学の研究 明治篇》,东京:吉川弘文馆1966年版。关于“文明史体”三原则的归纳和阐释,见该书页198-214。
[23] 末广重恭《支那开化小史跋》(1883年10月),载田口卯吉《支那开化小史》卷末,东京:经济杂志社1887年第2版合本。“勃克尔”即巴克尔,“斯边撒”即斯宾塞。
[24] 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37页。
[25] 转引自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7页。
[26] 彬彬(徐彬)《梁启超》,引自夏晓虹编校《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27] 这是借用梁启超《东籍月旦》对日人田口卯吉所著《支那开化小史》的评语。
[28] 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梁启超提到参考了浮田和民的《日本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理想》等著作,对浮田和民的帝国主义倾向有了解。见中国之新民《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第2号,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
[29] 梁启超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见《清议报》第95册,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一日。
[30] 有贺长雄著、璱斋主人译《社会进化论》,见《清议报》第47册,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一日。
[31]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东籍月旦·第二章 历史》,《新民丛报》第11号,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32] 王舟瑶述《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二编,光绪二十八年京师大学堂年铅印本。
[33] 梁启超《东籍月旦》,《新民丛报》第11号,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34] 在张之洞主导的“癸卯学制”中,也颇有强调历史与地理、人种关系的内容;但张之洞一派与日本学界存在直接联系,其吸收“文明史”观点,未必通过梁启超的渠道,故在此忽略不论。
[3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6、89页。
[36]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三·论正统(悬谈一)》,《新民丛报》第11号,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一日。
[37]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五·论书法(悬谈二)》,《新民丛报》第16号,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
[38] 中国之新民《新史学二·第二章 史学之界说》,《新民丛报》第3号,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一日。
[39] 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凌曙注《春秋繁露》卷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6页。
[40] “三科九旨”内涵复杂,历来多有异说,此处仅概括最为普通的含义。参见《春秋公羊传疏》引何休《文谥例》、及《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年“春公会戎于潜”、三年“春王二月”等处何休解诂,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第2195下、2200中、2202中、2203中等页。
[41]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页。
[42] 康有为早年撰《教学通义·春秋》篇,有《春秋》以后“君日尊,臣日卑”的“三世”之说:“自晋至六朝为一世”、“自唐至宋为一世”、“自明至本朝”为一世。《万木草堂口说·学术源流(七)》亦有两条提到“三世”:“以天下分三等:一等为混沌洪蒙之天下,一等为兵戈而初开礼乐之天下,一等为孔子至今文明大开之天下,即《春秋》三世之义也。”又:“《春秋》分三世,有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乱世无可得而言,治升平世分三统:夏、商、周,治太平世亦分三统:亲亲、仁民、爱物。”此时康有为以孔子以后即为“太平世”,包含“亲亲”、“仁民”、“爱物”三统,与后来在《礼运注》、《孟子微》等著作中持论大异。分别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第40页;《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99-100页。
[43] 夏曾佑《答宋燕生书》(光绪二十一年四月),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30-531页。
[44] 严复《与梁启超》一(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严复全集》第8册,第119页。
[45]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10页。按:这里所说“大箸”,即《天演论》。
[46] 同前注,第108-109页。
[47] 梁启超《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时务报》第41册,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
[48] 《春秋董氏学》卷二,《康有为全集》第2集,第324页。
[49] 同前注,第323页。
[50] 徐勤《地球大势公论序》,《知新报》第2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51] 《交涉书目提要·万国公法四卷》,见《湘学新报》第8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一日。
[52] 欧榘甲《春秋公法自序》,《知新报》第38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53] 谭嗣同《与唐绂丞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4页。
[54] 《史学第三·论各国变通政教之有无公理》,《湘学新报》第5册,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一日。
[55] 梁启超《学校馀论(变法通议三之馀)》,《时务报》第36册,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同一段落,又见同时期梁启超所撰《上南皮张尚书书》、《与林迪臣太守书》等篇。
[56]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文野三界之别》,《清议报》第27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此文是对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以西洋文明为目标》一章相关文字的译述。
[57] 梁启超《论支那宗教改革》,《清议报》第19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58] 任公《饮冰室自由书·论强权》,《清议报》第31册,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59] 任公《中国史叙论》第八节“时代之区分”,《清议报》第91册,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一日。
[60] 参见《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休解诂,《十三经注疏》本,第2200中页。
[61] 刘逢禄《释三科例上·张三世》,《刘礼部集》卷四,道光十年思误斋序刻本,第1a-1b页。
[62] 梁启超《读春秋界说》上,《清议报》第6册,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六日。
[63] 皮锡瑞《论春秋借事明义之旨》,见《经学通论》四,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2页。
[64] 任公《中国史叙论》第七节“史以前之时代”,《清议报》第91册,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一日。
[65] 任公《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清议报》第100册,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66] 章太炎、孙宝瑄对“三世说”的接受,参见《孙宝瑄日记》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十四日、十八日诸条,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74-176页。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师培发表《周末学术史序·社会学史序》,以为“中国社会学,出于《大易》、《春秋》”,基本上是搬用章太炎《〈社会学〉自序》和《中国通史略例》的观点,但讲到“《春秋》通于社会学”时,则转以“三世说”附会“人群进化之迹”。见《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文章转载自公众号“社会理论”
作者简介
陆胤,1982年生于江苏苏州,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专研近世中国文学及相关思想文化史,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著有《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2015)、《国文的创生:清季文学教育与知识衍变》(2022)等学术专著,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微信号:zhanghuangguoxue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谢琰 董京尘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飞机打多了该怎么补回来(飞机打多了怎么补回来)
飞机打多了该怎么补回来(飞机打多了怎么补回来)
 第五人格紫皮兑换码有哪些 第五人格紫皮兑换码大全2023
第五人格紫皮兑换码有哪些 第五人格紫皮兑换码大全2023
 也门为什么那么乱(也门那么乱的问题)
也门为什么那么乱(也门那么乱的问题)
 中国bgmbgmbgm老妇在线:为你提供精挑细选抢先体验!
中国bgmbgmbgm老妇在线:为你提供精挑细选抢先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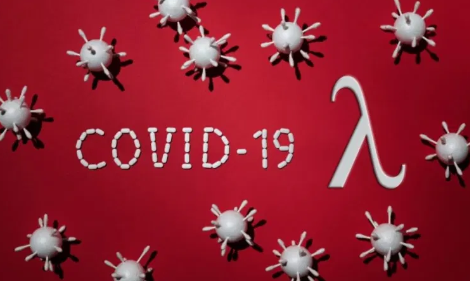 新冠病毒在物体表面可以存活多久(新冠病毒在物体表面可以存活多久2022)
新冠病毒在物体表面可以存活多久(新冠病毒在物体表面可以存活多久2022)
 抖音退货接口数据返回为空怎么办 抖音退货接口数据返回为空解决办法
抖音退货接口数据返回为空怎么办 抖音退货接口数据返回为空解决办法
大家好,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抖音退货接口数据返回为空怎么办 抖音退货接口数据返回为空解...
 蟒蛇是几级保护动物(蟒蛇是几级保护动物捕杀判几年)
蟒蛇是几级保护动物(蟒蛇是几级保护动物捕杀判几年)
蟒蛇是几级保护动物?蟒蛇是一种大型爬行动物,也是这个世界上比较原始的蛇种之一,是一...
 博德之门3养育间的雕像怎么转动(天刀云上之城星霜潭猴子雕像怎么转动)
博德之门3养育间的雕像怎么转动(天刀云上之城星霜潭猴子雕像怎么转动)
《博德之门3》是拉瑞安推出的一款角色冒险游戏,游戏最近新上线了正式版本。养育间是游戏...
 同比和环比的区别(同比和环比的区别公式)
同比和环比的区别(同比和环比的区别公式)
同比和环比的区别是什么,下面就由小编为大家解释一下同比增长和环比增长区别是什么的相...
 玩梗高手八二新婚日怎么过 玩梗高手八二新婚日通关攻略
玩梗高手八二新婚日怎么过 玩梗高手八二新婚日通关攻略
玩梗高手八二新婚日关卡里,需要玩家从图中找出十二处不合理的地方,小编带来玩梗高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