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界的中国美术史》,赖毓芝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年11月。当地球另一端的日常碎片不断成为地球这一端的日常谈资时,可知每个人都已深度嵌入全球化的浪潮。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透过知识社会
《跨界的中国美术史》,赖毓芝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2年11月。
当地球另一端的日常碎片不断成为地球这一端的日常谈资时,可知每个人都已深度嵌入全球化的浪潮。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透过知识社会学的目光,这句话可译为“一切历史叙事都离不开叙事者所处时代的滤镜”。一旦全球化滤镜成为主宰当代人的基本语法后,言谈者凡开口就必镶上全球化的“关怀”。由赖毓芝所著的《跨界的中国美术史》就是一部定位为全球化之作的中国艺术史。
《跨界》是一部论文集,汇集了作者自2001至2018年间陆续发表的十五篇论文,并按照主题相似性将其分置于上编“什么是异域”、中编“跨界的媒介与新框架的出现”、下编“选择与转换”等三组议题之中。赖取“跨界”为名的理由有二: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流动社会,中国器物是流动性的结晶以及中国艺术史蕴含了跨时空性;第二,身处全球化时代的艺术史研究应超越地域性,从静止的器物中挖掘出流动的世界。
根据赖毓芝的说明,上编主要探讨中国艺术如何想象与呈现“异域”以及“异域”如何作为一种处理现实问题的修辞;中编主要探讨作为新媒介与新认知框架的中国艺术如何在与异域的互动中展开;下编主要从艺术接收的角度讲述观众如何选择性地接受、消化并转换来自异域的元素。作者研究多以个案展开,写作中不断游走于自我与他者之间,通过多文本引证和图像对比,展示了其旁征博引和以小见大的能力。
但是,旁征博引和以小见大不见得可靠。赖的跨界只是在挑一些含有多种要素的器物作解读,至于其提出的结论也多是充斥“可能”与“大概”等模糊语词的探索性论断而非可接受交叉性验证的因果性说明。按我的看法,由于缺乏方法论自觉,赖始终没有跨出由前人框定的学术边界。下文将先简述《跨界》的写作逻辑,而后再对其展开批判性分析,最后会在结论部分简单提一下本人关于跨界的看法。
《跨界》的写作逻辑
《跨界》的研究多从半解读、半考据式问题展开。例如,第一篇文“想象异域”讨论的是“传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为何出自北宋末年而非南宋人陈居中所作”;第七篇文“‘苏州片’与清宫院体的成立”讨论的是“中西合璧的作品中哪些要素是‘西’的,哪些要素是‘中’的”;第十三篇文“知识、想象与交流”讨论的是“南怀仁的《坤舆全图》引鉴了哪些域外动物,它们分别代表了何种欧洲地理与自然史知识”。
解读和考据都起步于“是什么”的问题。所谓解读,就是定位作品赖以存在的话语空间。例如,解读《文姬归汉图》有窄宽之分,既可以将其窄解读为特定故事的视觉记载,也可像赖毓芝那样,将其宽解读为内亚政治关系的视觉表征。所谓考据,就是明确作品在特定话语空间下所处的位置。例如,赖将传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定位于北宋末年,通过风格分析和图像对比,指出其表征的是“北宋上至宫廷下至寻常百姓对北方异族文化的着迷与兴趣”。
《文姬归汉图》(局部),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解读与考据并不排他,但具体研究中有主次之分。将解读和考据置于“后发学者挑战先发学者”的框架下,可知研究者采用何种路径作主导取决于其所处的学术生态位。一般而言,如果一件作品的现有解读较多、相关论述考据较少,后发学者就更注重考据,尝试增加考据以坐实某种解读的唯一性,但如果一件作品的现有解读较少、相关论述考据充实,那后发学者就会从解读切入,力求借新解读以削弱现有考据的必要性。
赖毓芝所选的分析对象多是一些诞生于国际流动结点的个案,这些个案受多元环境影响。对研究而言,多元意味着排列组合的可能性更多、可解读的空间更大,因此策略上,赖的研究以解读为主、考据为辅。其具体操作可分两步:第一步,先采纳某一涵盖性视角定位研究对象;第二步,把该对象置于某一集合下,将其与该集合下的其他同类对象作对比或参照,通过拉开或拉近相互间距离以坐实其涵盖性定位。
篇幅有限,仅举两例以说明。第十五篇文“上海北斋”中,赖将任伯年的《钟进士斩狐图》解读为中国画家在日学东渐影响下、以日本技法绘制中国母题的画作。论证上,为拉远任作与传统的距离,赖将任作中的钟馗形象与传统图像作对比,指出传统图像不以冲突性构图方式刻画钟馗,而与此同时,为拉近与日本的距离,又将其与歌川国芳的《病关索杨雄》以及日本新闻图像作参照,指出冲突性构图是日本图像制作的惯例。
第八篇文“康熙的算学到奥地利哈布斯堡收藏的一些思考”中,赖将清宫收藏化石、贝壳、科学仪器、时钟等器物的行为解读为清宫国际化的体现。论证上,赖先指出清宫收藏了一些非书画传统的多元器物,以示读者这是“一种新的、有别于汉传统的价值体系之出现”,而后用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收藏作参照,指出两者的相似性,最后再将多元化收藏还原至欧洲的奇品收藏室传统,以说明如此收藏行为是国际化的附随物。
相比于其他中国艺术史写作而言,赖的研究有两层积极含义:第一、扩展了视野。传统研究者多采取近距离考察方式,将视野停留在制作者、观众、赞助人和收藏人的集体互动上,但赖拉长观察距离,建立起了跨区域经验之间的联系;第二,平衡了偏见。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国家,难以吸收和消化外来要素,但赖通过指出中国艺术个案中的国际性元素,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保守与封闭的“刻板印象”。
(清)任颐《钟进士斩狐图》。
《跨界》的问题
艺术史是历史学分支,虽方法论无异,但分析对象有异,历史学聚焦于文字材料,艺术史以器物为中心。理论上,两者应结合,但在操作过程中,出现分流。相比于文字,器物的意义在于能够提供更为直观的现象学经验。但是,也正因器物在艺术史家眼里过于聚焦,以至大多数艺术史家的目光都无法超越器物设定的边界。赖毓芝有意做出一些超脱性尝试,但依我见,并不成功,原因有四。
第一,问题意识不明确。《跨界》的研究围绕“是什么”展开,回答这类问题的关键是特定视角的选取以及基于该视角的定义、分类与测量。操作上,研究者只要在行动者、网络、组织、文化、过程等视角中任选一个,就可炮制同类叙事。《跨界》选择全球化的过程视角,其所有结论都可简化为:某器物是全球流动的结晶,其反映的是中原世界在某一时期的国际性。但是,这些研究都未上升至因果性论证以至于视角的选择显得多余。
读者只需反问“什么器物不是全球流动的结晶”“中国哪段历史纯然断绝了国际流动”“什么器物不能反映国际性”以及“反映了如何,不反映又如何”等问题,就可发现此类研究的尴尬。对读者而言,如果无法说明某一视角的必要性,那“用全球眼光看《文姬归汉图》”与“用中国眼光看该图”的差异如同“老虎看豹子”与“猫看豹子”的差异,都可以,也都无所谓。
其实,视角只有在以解释为目标的研究中才会显现,因为解释性目标指向单一。例如,在回答“传陈居中《文姬归汉图》中的外族服饰有哪些特色”这一问题时,回答者无论基于何种视角作答都无所谓,因为该问题本身开放。但问题若改为“为什么传陈居中的《文姬归汉图》中的外族服饰会比其他版本的《文姬归汉图》中的外族服饰有更高的多样性”,基于过程视角的回答就会胜出,因为多元本身往往是流动的后果。
第二,解读作品过于依赖心理感受。第四篇文“再现边疆”中,作者仅根据任伯年所作的《苏武牧羊图》与黄慎的《苏武牧羊图》中苏武面向的差异,即前者回望,后者前视,就推测任伯年的内心世界是焦虑;在第一篇文“想象异域”中,仅根据《文姬归汉图》中存在属于辽式和金式着装和用器以及其他学者有关北宋民间辽风、金风流行的说明,就断定该画展现的是“北宋上至宫廷下至寻常百姓对北方异族文化的着迷与兴趣”。
(清)黄慎《苏武牧羊图》。
(清)任颐《苏武牧羊图》。
“焦虑”“着迷与兴趣”说都是不可追踪的心理还原论,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作者自身的心理投射。以《文姬归汉图》为例。就经验与认知的关联性而言,在一幅有关汉代母题的宋版绘画中用辽式与金式的视觉符号刻画匈奴,必定意味着绘画者挪用了自己的日常经验。但是,“这些视觉符号为何会进入绘画者的日常空间并成为被挪用对象”是一个需要考察市场、传播、朝贡体系运作的经验性问题,而非心理学问题。
历史资料缺乏不是心理学介入的理由。依我看,制画者的眼光受宫廷经验的形塑,而宫廷经验的形成是足量的外族贡品在宫廷内累积的结果。相比于赖的说法,我的说法有三点优势:第一、一切围绕事实判断展开,避免了价值偏好;第二、无须揣摩历史行动者的动机;第三、设定了经验限度,提供了信息追踪的方向。我这么说并非想否认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中的意义,而是想提醒读者,心理推测只能作猜的线索而非写的语法。
第三,缺乏追踪特殊性的眼光。《跨界》中的案例都是全球流动结点中的“中国案例”,但整部作品并没有呈现出任何有关人、网络或文化的“中国性”。如第十篇文“从杜勒到清宫”中,作者介绍了犀牛图像在十七、十八世纪从印度传至欧洲而后再传至清朝的过程,指出犀牛在欧洲非常风靡、化身成各种奢侈品装饰,但在清宫,其只不过是一只不可理解的异兽。这段叙事平淡无奇,因为它展现的是大多数传播活动的常态。
就传播机制而言,任何一件事物传到域外成为一个热点现象都是小概率事件,因为不同空间之间存在话语隔阂。十七、十八世纪的中国信息流动缓慢,自己的文化本体又非常深厚,以为整个域外都是蛮夷世界,所以对外部世界缺乏好奇是一件正常之事。挖掘特殊性需要构建反常案例,但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犀牛不流行算不得什么反常。不反常,就不值得书写。
对读者而言,只有提供反常或逆向现象的说明才会呈现特殊性。作者在写作时也确实提及了两个有趣现象,即(1)晚商、战国甚至到唐代的犀牛形象比起宋代以后本草系统的犀牛都较接近事物,但是宋代以后走下坡路,以及(2)虽然犀牛没有在中国宫廷内流行,但是作为域外事物的大象却曾流行过。这两个比较现象都呈现出了某种令人好奇的反转,但作者只是一笔带过而已。
第四,不具备抽象化的能力。历史是结构、权力、行动者和机制等条件汇聚的结果,器物是历史过程遗留下来的碎片。赖的大多数研究都只停留在碎片上,而没有用碎片编织出更宏大的图景。个人认知的层面看,这是因为作者眼光局限,没有宏观想象力。从学科的层面看,这是因为艺术史研究本身都以器物为本体,研究目光被锁定在了具体器物上,削弱了构建宏大叙事的可能性。
整书下篇部分共有六篇文章,其中五篇都是关于传教士将西洋知识传至清宫并转化成清宫制品的故事,但这些知识都是动植物内容而非基督教内容。为什么传教士传播动植物内容?传播这些内容跟传教有关吗?如果有关,这是传教的特殊策略还是一种普遍性策略?传教有哪些可行的策略?作者关注到了行动者、器物,也关注到了传教活动本身,但却没有将这些整合起来以构建一套更为完整的叙事以同时回答上述问题。
传教策略有多样。教士团在有些地方只采取撒钱、鞭打等硬方式;有些则只采取套近乎、供礼、东拉西扯等软方式;有些则软硬兼施。传教士团体在不同地方会采纳不同的策略类型以及策略配比,因为策略实施需因地制宜。不同的策略方案会催生不同的器物,好的研究往往能透过器物样式识别传播策略,并根据传播策略的分布进一步推测不同空间的生态差异,即实现从微观至宏观的“跨界”。然而,作者并没做到这一点。
“跨界”何以可能?
全球化视野下的历史研究过去几十年一直是热门。葛兆光在《读书》中一篇有关全球史的短文中,指出目前全球史写法有两种:一种是满天星斗式研究,另一种则是台球撞击式研究。满天星斗式研究属于大杂烩,如著名的《詹森艺术史》,台球撞击式研究就是以特定对象的流动为核心,将不同地区的事件、人物、现象之间的互动相结合的叙事。赖的写作属于后一种。
但是,无论哪一种研究都显得很笨拙。这种笨拙源于二战后研究范式与全球化议题之间的冲突。二战后的研究开启于贡布里希。贡布里希为反思二战前的理性主义思潮,有意弱化宏大的艺术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对艺术家自主性的强调。贡布里希的继承者更倾向于从微观出发。但是,全球化的议题往往依赖于宏大的想象,需要探索超越具体器物的宏观结构与力量。
赖就是因为处理不好两边的诉求,所以全球化在其叙事中只是一个先验视角而非经验视角。殊不知,没有可靠的研究问题,就不会生成适宜的方法、数据与视角。对于疾病的研究不可能在现象观察、案例对比、解释目标明确之前就在流行病学视角、组织学视角、细胞学视角和分子生物学视角之间做抉择。简言之,提出一个可回答的研究问题是赋予视角正当性的唯一方式。
我对赖提出的四个批评其实都可归结为一点,即赖无法提出可回答的、能够尽可能缩小解读空间的研究问题。赖有很强的文献索引能力,这一能力在前互联网时代很必要,但在Google(谷歌)一代已经被削弱了一大截,如今已经到了ChatGPT(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时代,作用将进一步缩减。但是,计算机再怎么进步也不会具备议题设置的能力。
赖的文章纵向跨度十八年,并在这十八年里不断重复自己,若不是长期拘泥于封闭的小圈子做研究,就是艺术史研究界本身就是一个较为封闭的小圈子。依我史学同事邱氏所言,将研究对象的跨界视作自己研究能力和视野的跨界是当前自认跨界学者善于偷懒的体现。我以为,艺术史研究者不妨好好思考一下自身学科的合法性。
撰文/陶力行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
 美美哒免费高清影院在线观看6优质版
美美哒免费高清影院在线观看6优质版
 烟雾报警器会闪红灯吗 烟雾报警器会不会闪红灯
烟雾报警器会闪红灯吗 烟雾报警器会不会闪红灯
 辣椒辣手最快解决办法(辣椒辣手多久会消失)
辣椒辣手最快解决办法(辣椒辣手多久会消失)
 蜂蜜水怎样喝减肥(蜂蜜水怎样喝减肥治便秘)
蜂蜜水怎样喝减肥(蜂蜜水怎样喝减肥治便秘)
 中国五大战区司令(中国五大主要战区明细)
中国五大战区司令(中国五大主要战区明细)
 三国志幻想大陆繁花之约怎么过
三国志幻想大陆繁花之约怎么过
小编为大家分享三国志幻想大陆繁花之约怎么过-三国志幻想大陆繁花之约全天攻略相关内容,...
 博德之门3基础属性魅力有什么(博德之门3选什么种族)
博德之门3基础属性魅力有什么(博德之门3选什么种族)
《博德之门3(Baldur s Gate 3)》中的基础属性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基础属性越高角色...
 蝙蝠的眼睛真的看不见吗(蝙蝠看不见还长个眼睛为什么)
蝙蝠的眼睛真的看不见吗(蝙蝠看不见还长个眼睛为什么)
蝙蝠的眼睛真的看不见吗?蝙蝠的眼睛是可以看见。蝙蝠分为两个亚目,大蝙蝠亚目中的绝大...
 汉字找茬王女生别进怎么过关
汉字找茬王女生别进怎么过关
为你提供女生别进的攻略信息,《汉字找茬王》是抖音上目前很火的精彩益智烧脑解谜闯关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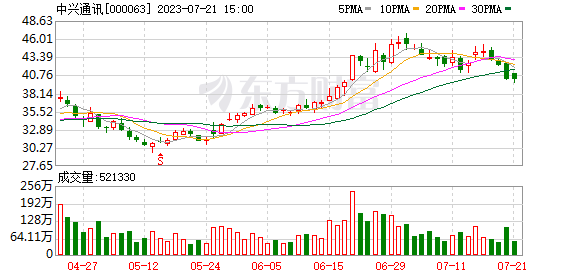 【图解牛熊股】AI概念惨遭主力抛弃 商超龙头狂飙超60%
【图解牛熊股】AI概念惨遭主力抛弃 商超龙头狂飙超60%
7月第三个交易周结束,三大指数集体调整,本周上证指数跌2 16%,深圳成指跌2 27%,创业...